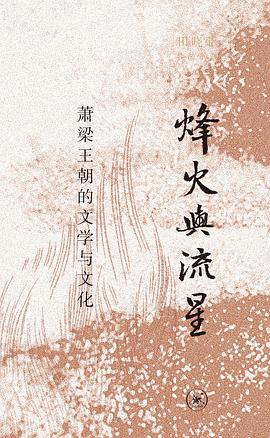烽火与流星 [图书] 豆瓣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9.2 (9 个评分)
作者:
田晓菲
2022
- 3
对梁人来说,他们的时代充满了崭新的开始,“新变”,及能量充沛的创举。他们生活在现下,完全沉浸于“此时与此地”,投入地经历每一个时刻。他们在智识上极为精微渊雅,精神上却又相当天真。对梁朝的文化精神最好的概括,不是“颓废”,而是“康强”。
梁朝覆灭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个世纪,它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份重要的遗产,但这又是一份让人感到不安的遗产,因为它和当代文化政治纠结在一起,展示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问题。曾经一度数量庞大的文本现在只有零星的残存,南方帝国的辉煌就隐藏在这些断简残篇之中,后人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对之进行诠释,这些带有隐含的动机与偏见的诠释更加扭曲了它们的光芒。
——田晓菲
在烽火与流星照耀下的国土,一半隐藏在阴影里,这正好是对萧梁王朝的最好象征。本书试图为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勾勒一副肖像画,不仅探讨梁朝的文学作品,更旨在检视梁朝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就此提出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史和文学史问题。
梁朝覆灭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个世纪,它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份重要的遗产,但这又是一份让人感到不安的遗产,因为它和当代文化政治纠结在一起,展示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问题。曾经一度数量庞大的文本现在只有零星的残存,南方帝国的辉煌就隐藏在这些断简残篇之中,后人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对之进行诠释,这些带有隐含的动机与偏见的诠释更加扭曲了它们的光芒。
——田晓菲
在烽火与流星照耀下的国土,一半隐藏在阴影里,这正好是对萧梁王朝的最好象征。本书试图为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勾勒一副肖像画,不仅探讨梁朝的文学作品,更旨在检视梁朝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就此提出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史和文学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