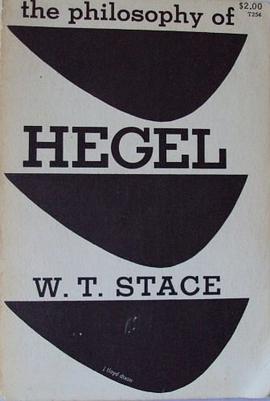# 第一部分 基本原则 第二章 现代哲学与黑格尔
亚氏之后,希腊唯心主义传统直到近代才重新出现,对黑格尔影响最大的近代哲学家是斯宾诺莎和康德。
## A. 斯宾诺莎与黑格尔
斯宾诺莎提出,一切规定即是否定。事物要“是”,它必然要“不是”。说某物是绿色的,就必须把它从粉色、蓝色等其他种种颜色事物的领域中排除。黑格尔颠倒了这一说法,提出一切否定即是规定。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暂且不讨论。
黑格尔的无限理论也深受斯宾诺莎影响。无限就是没有限制,那就是没有被规定,没有被规定当然就是空洞的,即“无”。这个“无”来源于斯宾诺莎的“实体”。
## B. 休谟与康德
希腊传统直接假设:人有能力认识实在。柏拉图和亚氏都没有对这一假设产生质疑,康德首次对其发问:什么是知识?知识何以可能?知识是否有其必然的界限?
而康德的疑问来自休谟的哲学思考——比如他对于因果性的思考。在休谟看来,因果性包含必然性和普遍性,而这两者都不能从经验中得到(休谟认为知识/观念/概念唯一来源是经验),所以因果性只是一种幻觉。
康德批判了休谟的思考。他首先重新考察了知识,认为知识来源于感性和理性,前者被动,后者主动,两者一同作用才产生知识。
感性方面,分为内感官和外感官,时间是前者的形式,时间和空间是后者的形式,感性只能告诉我们个别事实。然而,我们的确拥有这样一些知识,比如“2+2=4”——从“这两个和那两个合起来是这四个”得来,“一对直线不能围成空间”——从“这一对直线不能围成一个空间”得来,这类知识超越了个别性,其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个别事实无法提供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先天综合命题一方面是时空的,一方面又是普遍必然的,这如何可能?答案只能是,时空是感性自身的形式,我们只能通过时空性去认识世界,所以,在只涉及时空性的命题上,它们是普遍必然的。如果命题在时空性上填充了内容,比如颜色、味道,那么普遍性和必然性立马就消失了,但是,在只涉及时空性的命题时,比如几何学和数学命题,它们有普遍必然性。
理性方面,存在同样的问题。把各种命题完全抽象成逻辑判断形式,可以得到康德所谓的知性范畴表。这些知性范畴是理性分析感性材料先天就有的概念框架。
康德的理论导向不可知论。时空性和知性范畴是纯粹形式、逻辑上先于一切经验,不来自于任何外部来源,而是心灵自身的结构。这使得我们只能去考察现象,因为实在不在时空中,知性范畴对它们也不适用,所以实在本身完全不可知。
## C. 从康德出发的哲学进路
后人彻底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和物自体概念,主张人有认识实在的能力。物自体的概念自相矛盾,因为如果我们断定它是感觉的原因,或者只是断定它存在,那也是对它使用了“存在”和“因果”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只能用于现象,我们既然知道它存在,并且是原因,它对我们就不是不可知的。
时空性和知性范畴如果不来源于任何外部,即物自体,那它们的来源只能和它们一样也是心灵的产物,既然连实在都是心灵/理性的产物,那我们可以断定,一切事物必定都可知。
## D. 对“不可知”观念的批判
哲学上的某物“不可知”指的是无论排除一切偶然条件,我们的心灵构造本身从根本上无法认识它。不仅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不可知”失败了,实际上,一切意义的“不可知”都是不可能的。
—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章节: 第一部分 基本原则 第二章 现代哲学与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