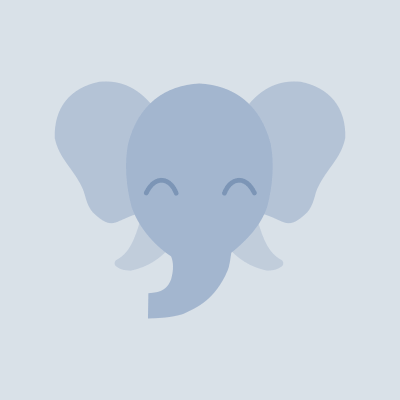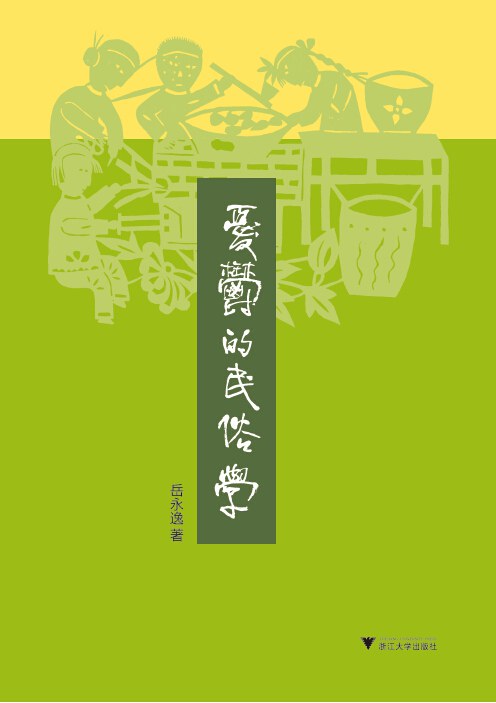读过 忧郁的民俗学 🌕🌕🌗🌑🌑
本书为发表在各种杂志上文章的结集之作,修改之后集结成书。
第一部分“急景凋年”系列文章的前7篇,从民俗学毕业生就业难,引出学科困境及其历史成因,引出了中国的民俗学历史。自诞生起,民俗学经历了在周作人时期做文学材料和顾颉刚时期做史学旁证,最后回到社会学的大伞下寄居,始终没有取得独立重点学科的地位。捎带写了汉学家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民俗学家地位尴尬,虽借着为民俗文化申遗的运动风光一时,但学科仍不具有力量。作者暗示本学科的学者对自身学科历史和学理的挖掘和继承态度默然,或是原因之一。后面的十几篇,大概可以用其母亲的拥有被害幻想症状的“虚病”,串联起民间医疗的方方面面,比如巫医的“倒痰”,家乡的风水,通灵的“走阴”,他作为知识分子对西医、中医/巫医的两头怀疑,从五四到80年代到当下的“弑父”-“寻父”-“造父与夸父”的文化流变,最终把母亲的病归结为与个人与社会的都市性与乡土的脱离和分裂。
第二部分“草根·小剧场·空壳艺术”算文艺批评吧,但评价的是表演形式而非内容。从相声历史上“平地抠饼”到当今的小剧场相声和屏幕上的“喉舌”相声对比。居然提出了“喉舌”相声距离人民更近的论点。大概是批评郭德纲的“天价”相声和电视上相声不花钱。可实际上知道郭德纲的人,多数也是在屏幕上。他批判小剧场的封闭,认为这是一场新的造神的牛皮。怀念民间赛社和革命剧场的“空的空间”。
第三部分“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延续了前面文章的“精英对比草根”视角,指出政府官员对老百姓没有情感,学者对民俗的视角做不到尊重的平视或学习的仰视。就如同第一部分第8篇中的事例,年轻设计师用形似倒头饭的雕塑迎元旦,遭老年人反对;两个群体的讨论针锋相对却不了了之,整个过程民俗学研究者没有反应。其中反应了民俗传承的断裂,对话的缺位,研究的失焦。
第四部分“大春节观”,围绕春节写了许多应该。政府应该,商家应该,设计师/艺术家应该,教育者应该,民间团体应该...在我看来,作者在这里陷入了自己所反对的精英的傲慢,仿佛民众自己不知道如何过节似的。
第五和第六部分是书评,前者评苏文瑜的介绍周作人的著作《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和《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后者评论北岛介绍其记忆中的北京的《城门开》。前者篇幅长些,大概因为周作人与民俗学的渊源。
本书在后记中有描述写作目的的两句话:“与其如说它是写给民俗的,不如说它是写给民的”,“向'母亲'和'土地'致敬的”。但就其行文风格来说,可以说距离民,土地,母亲都很远。无法走进母亲的内心,回不去自己的乡土,脱离了草根又不喜欢精英的作者,处于焦虑无着的状态下,用着小民无法听懂的语言,用批评者、观察者的姿态进行着精英的书写。
我是从看到“漫漶”二字起,感觉不妙的。但因为是在别人写的前言里出现的,怪不到作者身上。于是接着看。很快看到了“瞽者”(意为盲人)二字。就觉得此书是那种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的知识分子书写。过于书面化的用语和表达,第一次见时,是《读书》杂志。当时还觉得《读书》的作者厉害,读书的人果然不一样。后来认识到,这要么是出于知识的诅咒,要么就是那些作者只想写给“自己人”看。“反精英”的文字,“精英”却味儿太浓,如同干嚼味精。忧郁的不是民俗学,忧郁的,是此种视角,此种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