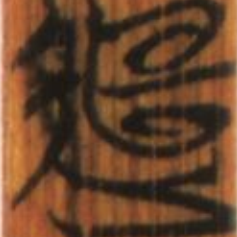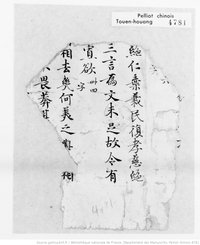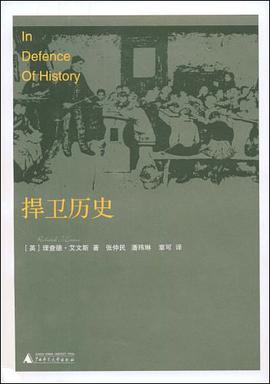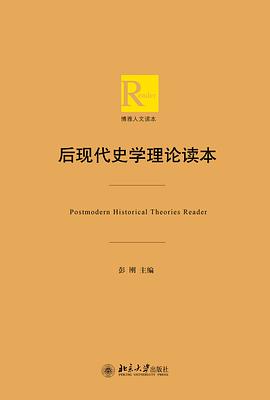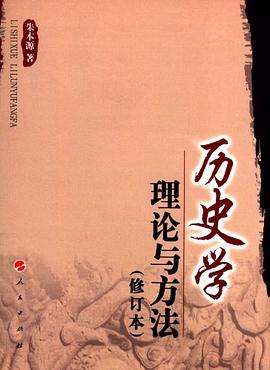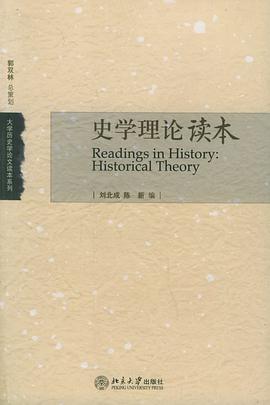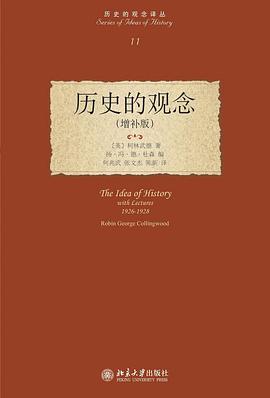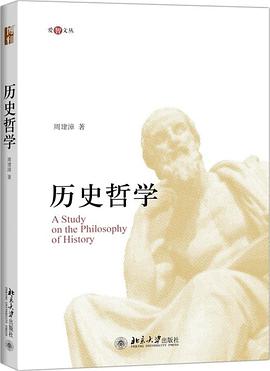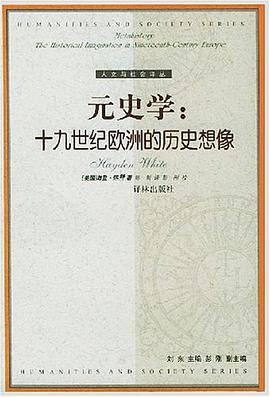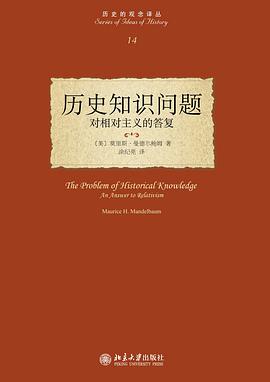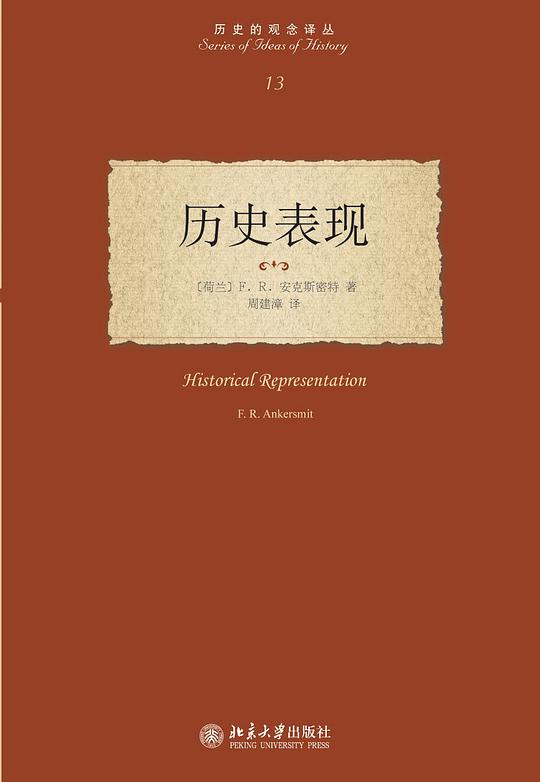史学理论
捍卫历史 [图书] 豆瓣
In Defense of History
8.5 (8 个评分)
作者:
理查德·艾文斯
译者:
张仲民
/
潘玮琳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2
在《捍卫历史》中,艾文斯从史学史的角度展开讨论,辅以其本人大量的实际研究经验,旁征博引、参照比对,既很好总结与反思了以卡尔与艾尔顿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乃至19、20世纪的史学史与史学思想,还讨论了材料、证据、因果关系、客观性等关键的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变化,有理有据地反击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进攻。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在本书中,艾文斯从史学史的角度展开讨论,辅以其本人大量的实际研究经验,旁征博引、参照比对,既很好总结与反思了以卡尔与艾尔顿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乃至19、20世纪的史学史与史学思想,还讨论了材料、证据、因果关系、客观性等关键的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变化,有理有据地反击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进攻。艾文斯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科,它更关注知识的内容而非本质,历史学家若是足够小心谨慎,客观的历史知识既是可以期望的,也是能够获得的。可艾文斯本人亦非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产生了许多有益影响,历史学家应该将这些有益的影响贯彻到当下的历史研究中。
目 录 :
导论
第一章 史学史
第二章 历史学、科学与道德
第三章 史家及其事实
第四章 材料和话语
第五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第六章 社会与个人
第七章 知识和权力
第八章 客观性及其局限
跋
进阶阅读书目
索引
译后记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在本书中,艾文斯从史学史的角度展开讨论,辅以其本人大量的实际研究经验,旁征博引、参照比对,既很好总结与反思了以卡尔与艾尔顿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乃至19、20世纪的史学史与史学思想,还讨论了材料、证据、因果关系、客观性等关键的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变化,有理有据地反击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进攻。艾文斯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科,它更关注知识的内容而非本质,历史学家若是足够小心谨慎,客观的历史知识既是可以期望的,也是能够获得的。可艾文斯本人亦非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产生了许多有益影响,历史学家应该将这些有益的影响贯彻到当下的历史研究中。
目 录 :
导论
第一章 史学史
第二章 历史学、科学与道德
第三章 史家及其事实
第四章 材料和话语
第五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第六章 社会与个人
第七章 知识和权力
第八章 客观性及其局限
跋
进阶阅读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图书] 豆瓣 谷歌图书
作者:
朱本源
人民出版
2012
- 4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西方历史思维模式的演进历程。作者探讨了“历史”的基本概念,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精彩的回答和阐述,回顾了百年来不同学术流派在历史编纂学方法上所采取的不同模式,尤其是追溯并分析了西方史学史中各重要时段历史思维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展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何兆武先生在序一中称“……《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之体大思精、庞征博引,于中国古代、西方现代以及苏联的有关著作均有精辟的论断,其体例与阐述之允当是值得每一个读者细细咀嚼的。”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由王成军教授修订整理。
历史的观念 [图书] 豆瓣
The Idea of History
9.5 (15 个评分)
作者:
[英] 柯林武德
译者:
何兆武
/
张文杰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
《历史的观念》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著作之一。此书为柯林武德遗作,最初于1946年由诺克斯编辑成书,极受学界关注。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由杜森编辑的《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澄清了诺克斯版编纂过程中的问题,并且增收了柯林武德在1926-1928年间所做的历史哲学讲演稿。篇幅增加三分之一,有助于读者了解柯林武德思想的原貌。
这部理论性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畅销书,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读者重视,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一,它要言不烦地梳理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念的演变,从古希腊到现代,各阶段的特征一目了然;二,作者兼有历史学和哲学两方面的思维训练,所论问题切中历史学的核心,不给人隔膜之感;三,作者思路明晰,语言简练,将深刻的哲学思想用平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
*
历史哲学这一课题的研究者,在近代西方是哲学家远多于历史学家,像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这样以哲学家而兼历史学家的人,并不多见。 ——何兆武
*
1926年和1928年的讲稿尤其重要,它们包含了柯林武德对其历史哲学思想所做的首次全面阐述。因此,通过它们,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第一阶段得到了完好记录。他后期历史哲学的许多著名观点都是在这些讲稿中第一次被阐述,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 ——扬•冯•德•杜森
这部理论性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畅销书,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读者重视,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一,它要言不烦地梳理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念的演变,从古希腊到现代,各阶段的特征一目了然;二,作者兼有历史学和哲学两方面的思维训练,所论问题切中历史学的核心,不给人隔膜之感;三,作者思路明晰,语言简练,将深刻的哲学思想用平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
*
历史哲学这一课题的研究者,在近代西方是哲学家远多于历史学家,像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这样以哲学家而兼历史学家的人,并不多见。 ——何兆武
*
1926年和1928年的讲稿尤其重要,它们包含了柯林武德对其历史哲学思想所做的首次全面阐述。因此,通过它们,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第一阶段得到了完好记录。他后期历史哲学的许多著名观点都是在这些讲稿中第一次被阐述,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 ——扬•冯•德•杜森
元史学 [图书] 豆瓣
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9.7 (7 个评分)
作者:
(美)海登.怀特
译者:
陈新
译林出版社
2004
- 11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历史哲学导论 [图书] 豆瓣
作者:
〔英〕沃尔什
/
W.H.Walsh
译者:
何兆武
/
张文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0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第一部分探讨历史思维的逻辑,亦即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的解释、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问题,第二部分探讨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是对历史的形而上学解说,或者说,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其意义何在。在历史哲学的学术史上,沃尔什最早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划分,而他本人的研究更为注重的是前者。可以说,沃尔什接续了布莱德雷、柯林武德的研究传统,将英国学者对于历史思维的哲学思考加以总结和提炼,正式奠定了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
沃尔什此书是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之后,英国哲学界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又一部名作,自1950年代问世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或翻印。中译本参酌原作不同版本,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均做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
这部小书,……在英语学术界有关“历史思维的逻辑”的讨论中,可谓一部最好的简明论著。尽管这本书首先是写给哲学研究者,而不是写给历史研究者的,不过,所有学历史的人,假如想对他们的学科有关反思的话,应该人手一册。——小约翰•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是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最好的一部总结之作。 ——威廉•德雷(William Dray)
沃尔什此书是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之后,英国哲学界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又一部名作,自1950年代问世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或翻印。中译本参酌原作不同版本,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均做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
这部小书,……在英语学术界有关“历史思维的逻辑”的讨论中,可谓一部最好的简明论著。尽管这本书首先是写给哲学研究者,而不是写给历史研究者的,不过,所有学历史的人,假如想对他们的学科有关反思的话,应该人手一册。——小约翰•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是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最好的一部总结之作。 ——威廉•德雷(William Dray)
历史人类学导论 [图书] 豆瓣 谷歌图书
作者:
雅各布·坦纳
译者:
白锡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0
写这本书的想法,是我在2001—2002学年的时候,因参与柏林科学讲座而逗留柏林期间产生的。在哈伦湖畔举行的那期讲座,气氛很是促人思考,而且富有跨学科挑战的特色。那种挑战性不仅给人带来了许多启发,而且还在理智上给人留下了某种没有核心的感觉。与会专家运用的是各种五花八门的专业语言,表现出科学之不统一当时每天都能体验到这种不统一。面对这种无法一目了然的局面,你该怎么办呢?难道你该重新退回自己学科的象牙塔里,以便在跨学科的混乱一团之中标明自己的明确立场?抑或你该冒着这样一种危险,就是可能给别人留下自己仿佛是个无忧无虑的科学百科业余爱好者似的,对一切都感兴趣?我曾试图避免做出这种非此则彼的选择,不过却明确地侧重了扩大我的视野。假如没有我在那年获得的种种启发和鼓励,我是根本写不成这本书的(从一个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本书涉足了许多不同的新领域)。因此,我想首先感谢那次柏林科学讲座。
2002年秋,我到了我在跨学科迷宫里从事科学活动的第二站,即设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是汉斯约尔格•莱茵贝格尔和米夏埃尔•哈格纳两位先生邀请我去的。所以我要感谢他们。我在那里工作期间,跟彼得•舍特勒尔先生进行的多次讨论,对我构想本书也十分重要。关于史学和大脑研究之间关联的初步思考,则是2003年春,我在柏林的马克•布洛赫中心的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在2003—2004学年的冬季学期,我享受了一次教授休假,并在巴黎的人文科学院逗留了一段时间。事实证明,那对我写作此书是一次极好的推动和促进。莫里斯•埃玛尔的邀请,把我从本国行政式的大学教学科研活动中解脱出来,再次为我提供了不受干扰地专事写作的机会。在那段时间,我跟好几位法国的史学家进行了交谈,特别是萨比娜•洛里加女士和该科学院研究员彼得•贝克尔先生,从而在这个课题上为我打开了新的眼界。
在澄清各种问题方面,埃贝哈德•奥尔特兰德)、多丽丝•考夫曼和瓦伦丁•格勒布纳,都曾是我的在行的谈话伙伴。另外,我从《历史人类学》杂志的编者同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给我启发的还有达维德•古格里)、米夏埃尔•哈格纳、米夏埃尔•汉佩和菲利普•萨拉赞,他们都是跟我一起在知识史研究中心(Competence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工作的同事。这个中心是苏黎世大学和瑞士联邦技术大学共同组建的一个机构,作为两校的合作项目。我们的这些讨论表明,历史人类学这种东西是一个有着多副面孔的题目,在这个题目里,许多现实性的争议层见叠出;而这些讨论,也展现了不少理论上的分歧。凡是我跟他们讨论过我这本书的那些人,都给我出过许多点子,只是我在书中并未专门标出是谁贡献的想法罢了;不过全书的论证线索,以及书中未予论述或仍未论述明白的问题,则全由笔者个人负责。在本书定稿的最后阶段,我很信赖出版社专心致志的编审部;此外还有阿里亚娜•温克勒女士,她在审阅我的书稿时不仅表现了形式上的一丝不苟,而且还证明她在内容方面也是在行的。
我在撰写此书期间,尤其是我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专事写作的那段时日里,真是如同不畏艰险地在崎岖不明的哲学思维小路上攀援摸索一样。多亏西蒙娜•马伦霍尔茨总是给我提供许多充满思想火花的点拨,才多次把我带回到坚实的思维道路上来。要不然的话,这部论及一个无边无际的课题的手稿怕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特向她专门致谢。
目录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Ⅰ
鸣谢/1
第一章 绪论:人类学的混沌状态/1
第一节虚拟世界里的食人者/1
第二节定义与分类/4
第三节问题与命题/10
第四节目的与结构/15
第二章 从启蒙运动时期的惊诧到1900年前后的危机意识/27
第一节历史学与人学/27
题外话:“机器先生”——拉美特利/30
第二节人类学与种族分类/33
题外话:福柯对人类学“睡眠”的批判/37
第三节世纪末的史学危机 /39
第四节体质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41
第三章 20世纪的历史学与人类学/53
第一节来自法国的革新:年鉴派史学家/54
第二节欧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径/61
第三节历史人类学在德国的发展趋势与论争 /63
第四节单页插图?档案馆里的田野考察与田野
考察时的寻踪觅迹/68
第四章 历史人类学的问题与视角/83
第一节“具体的人”是虚构吗?/83
第二节微观史学与行为理论/86
第三节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以及“等级游戏”/93
第四节日常、习惯、重复结构:稳定与演变/99
第五节肉体体验与身体技术/102
第五章 从自然科学研究看人/119
第一节关于“尚未确定的动物”的若干论断/119
第二节社会生物学的归纳与进化论的普遍化/123
第三节大脑里的文化:神经学认识 /127
第四节有限理性与日常启发学/131
第五节跨学科对话的问题与机遇/134
第六章 历史与对称人类学/147
第一节 循环性与相互作用/148
第二节 劳动与媒介:制造工具的动物之作为符号动物/150
题外话:文字之作为传播媒介和人类实践/154
第三节 信息论、控制论人类学、技术/156
第四节 理解的可能与局限/159
结 语 “理性的人”/169
参考文献/175
译者附语/227
2002年秋,我到了我在跨学科迷宫里从事科学活动的第二站,即设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是汉斯约尔格•莱茵贝格尔和米夏埃尔•哈格纳两位先生邀请我去的。所以我要感谢他们。我在那里工作期间,跟彼得•舍特勒尔先生进行的多次讨论,对我构想本书也十分重要。关于史学和大脑研究之间关联的初步思考,则是2003年春,我在柏林的马克•布洛赫中心的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在2003—2004学年的冬季学期,我享受了一次教授休假,并在巴黎的人文科学院逗留了一段时间。事实证明,那对我写作此书是一次极好的推动和促进。莫里斯•埃玛尔的邀请,把我从本国行政式的大学教学科研活动中解脱出来,再次为我提供了不受干扰地专事写作的机会。在那段时间,我跟好几位法国的史学家进行了交谈,特别是萨比娜•洛里加女士和该科学院研究员彼得•贝克尔先生,从而在这个课题上为我打开了新的眼界。
在澄清各种问题方面,埃贝哈德•奥尔特兰德)、多丽丝•考夫曼和瓦伦丁•格勒布纳,都曾是我的在行的谈话伙伴。另外,我从《历史人类学》杂志的编者同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给我启发的还有达维德•古格里)、米夏埃尔•哈格纳、米夏埃尔•汉佩和菲利普•萨拉赞,他们都是跟我一起在知识史研究中心(Competence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工作的同事。这个中心是苏黎世大学和瑞士联邦技术大学共同组建的一个机构,作为两校的合作项目。我们的这些讨论表明,历史人类学这种东西是一个有着多副面孔的题目,在这个题目里,许多现实性的争议层见叠出;而这些讨论,也展现了不少理论上的分歧。凡是我跟他们讨论过我这本书的那些人,都给我出过许多点子,只是我在书中并未专门标出是谁贡献的想法罢了;不过全书的论证线索,以及书中未予论述或仍未论述明白的问题,则全由笔者个人负责。在本书定稿的最后阶段,我很信赖出版社专心致志的编审部;此外还有阿里亚娜•温克勒女士,她在审阅我的书稿时不仅表现了形式上的一丝不苟,而且还证明她在内容方面也是在行的。
我在撰写此书期间,尤其是我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专事写作的那段时日里,真是如同不畏艰险地在崎岖不明的哲学思维小路上攀援摸索一样。多亏西蒙娜•马伦霍尔茨总是给我提供许多充满思想火花的点拨,才多次把我带回到坚实的思维道路上来。要不然的话,这部论及一个无边无际的课题的手稿怕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特向她专门致谢。
目录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Ⅰ
鸣谢/1
第一章 绪论:人类学的混沌状态/1
第一节虚拟世界里的食人者/1
第二节定义与分类/4
第三节问题与命题/10
第四节目的与结构/15
第二章 从启蒙运动时期的惊诧到1900年前后的危机意识/27
第一节历史学与人学/27
题外话:“机器先生”——拉美特利/30
第二节人类学与种族分类/33
题外话:福柯对人类学“睡眠”的批判/37
第三节世纪末的史学危机 /39
第四节体质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41
第三章 20世纪的历史学与人类学/53
第一节来自法国的革新:年鉴派史学家/54
第二节欧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径/61
第三节历史人类学在德国的发展趋势与论争 /63
第四节单页插图?档案馆里的田野考察与田野
考察时的寻踪觅迹/68
第四章 历史人类学的问题与视角/83
第一节“具体的人”是虚构吗?/83
第二节微观史学与行为理论/86
第三节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以及“等级游戏”/93
第四节日常、习惯、重复结构:稳定与演变/99
第五节肉体体验与身体技术/102
第五章 从自然科学研究看人/119
第一节关于“尚未确定的动物”的若干论断/119
第二节社会生物学的归纳与进化论的普遍化/123
第三节大脑里的文化:神经学认识 /127
第四节有限理性与日常启发学/131
第五节跨学科对话的问题与机遇/134
第六章 历史与对称人类学/147
第一节 循环性与相互作用/148
第二节 劳动与媒介:制造工具的动物之作为符号动物/150
题外话:文字之作为传播媒介和人类实践/154
第三节 信息论、控制论人类学、技术/156
第四节 理解的可能与局限/159
结 语 “理性的人”/169
参考文献/175
译者附语/227
历史表现 [图书] 豆瓣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作者:
(荷) 安克斯密特 (F. R. Ankersmit)
译者:
周建漳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9
“表现”原本是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范畴,安克斯密特将之引入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叙述就像肖像画,它不是有关对象的摄影反映,因而不能充当证件照,但却是人物风神的丰富表现。作者在本书中从“史学理论”、“历史意识”、“史学理论家”三个层次,系统讨论了他的历史表现理论,反映了历史哲学领域的前沿进展。
本书充分认识到,历史写作在满足理性的、科学的探究要求的同时,审美也是其内在固有的要素。为了恰当理解历史写作的性质,应该区分表现与描述,并且以表现概念为核心,重新来定义诸如意义、真理和指称等传统的语义学工具。
本书的目的,是要在历史研究的文学进路之铺张与实证研究之节制中间界定并探寻某种中道。这一思路导向了历史研究的一种理性主义美学,在重申历史写作的审美维度的同时,也再次肯定了历史学科之合理性。
本书充分认识到,历史写作在满足理性的、科学的探究要求的同时,审美也是其内在固有的要素。为了恰当理解历史写作的性质,应该区分表现与描述,并且以表现概念为核心,重新来定义诸如意义、真理和指称等传统的语义学工具。
本书的目的,是要在历史研究的文学进路之铺张与实证研究之节制中间界定并探寻某种中道。这一思路导向了历史研究的一种理性主义美学,在重申历史写作的审美维度的同时,也再次肯定了历史学科之合理性。
普通语言学教程 [图书] 豆瓣 谷歌图书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5th ed., 1949)
9.3 (36 个评分)
作者: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译者:
高名凯
商务印书馆
1980
- 11
本書是著者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是本世紀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他在1857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法國人家裡。中學畢業後,於1875年至1876年在日內瓦大學讀了一年,其後轉學到德國,在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那時正是新語法學派諸語言學家和他們的教師古爾替烏斯(G.Curtius)對語言學問題辯論得最激烈的時候。他起初完全站在新語法學派一邊,在奧斯脫霍夫(H. Osthoff)和雷斯琴(A. Leskien)的指導下從事歷史比較語言研究工作,於1878年寫出他那篇傑出的《論印歐系語言元音的原始系統》,使老一輩的語言學家大為驚奇。
论文字学 [图书] 豆瓣
作者:
[法国] 雅克·德里达
译者:
汪堂家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5
序言
第一部分 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
题记
第一章 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
计划
能指与真理
写下的存在
第二章 语文学与文字学
外与内
外是内
接缝
第三章 论作为实证科学的文字学
代数:奥秘与透明
科学与人名
字谜与各种起源的协同性
第二部分 自然、文化、文字
“卢梭时代”导言
第一章 文字的暴力:从莱维―斯特劳斯到卢梭
专名的战争
文字与人对人的剥削
第二章 “这种危险的替补……”
从盲目到替补
替补之链
过度。方法问题
第三章 《语言起源论》的起源与结构
1.《语言起源论》的地位
文字、政治堕落与语言学堕落
当前的争论:关于怜悯的结构
最初的急诊与《语言起源论》的写作
2.模仿
间隔与替补
版画与形式主义的模糊性
文字的循环
3.发音
“指挥棒的运动……”
起源的铭文
圣歌
“手指的简单动作”。文字与乱伦禁忌
第四章 从替补到起源:文字理论
原始的隐喻
历史与文字系统
字母与绝对的再现
定理与戏剧
起源的替
第一部分 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
题记
第一章 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
计划
能指与真理
写下的存在
第二章 语文学与文字学
外与内
外是内
接缝
第三章 论作为实证科学的文字学
代数:奥秘与透明
科学与人名
字谜与各种起源的协同性
第二部分 自然、文化、文字
“卢梭时代”导言
第一章 文字的暴力:从莱维―斯特劳斯到卢梭
专名的战争
文字与人对人的剥削
第二章 “这种危险的替补……”
从盲目到替补
替补之链
过度。方法问题
第三章 《语言起源论》的起源与结构
1.《语言起源论》的地位
文字、政治堕落与语言学堕落
当前的争论:关于怜悯的结构
最初的急诊与《语言起源论》的写作
2.模仿
间隔与替补
版画与形式主义的模糊性
文字的循环
3.发音
“指挥棒的运动……”
起源的铭文
圣歌
“手指的简单动作”。文字与乱伦禁忌
第四章 从替补到起源:文字理论
原始的隐喻
历史与文字系统
字母与绝对的再现
定理与戏剧
起源的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