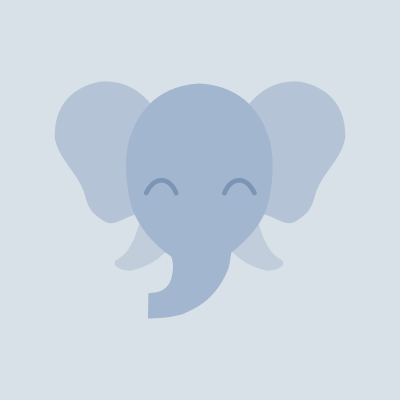那个少年
能遇到这本书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大抵是瞥到腰封上那句紫金陈的推荐,喜欢推理小说的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然而事实证明本书与推理悬疑毫无关系。正当我垂头而归时再蓝黑配色的封面上有恐惧、少年等词,又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狂喜,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这类题材的。
封面的山脊上默默写着两句话“一趟从群山间走进内心的的旅程,一段从治疗室走向世界的冒险”,这两句话也就是小说并行的两条主线。依我看来小说的前面着重于张朋城线的描写,而后面偏重于拉达克之旅线的感悟,相比之下我还是着重于前者。小说开篇扑面而来浓浓的台湾语言习惯,尤其是很多名词直接用英文来表述,不禁直接代入台剧的感觉。
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是藏族的传统地区,现在绝大部分处于印度的控制下。从列城宫殿到看未来佛再到贝图寺,(他们提到的曼陀罗,一般称为坛城沙画,曾在人文纪录片《轮回》《天地玄黄》中看过,很是震撼。)当想要向大师寻求什么结果时,收到比较哲学的回复:我没办法告诉你该往哪里走,我能做的只是让你继续你的旅程。
张朋城线其实又可分为两部分——医生之间,与朋城对话。医生之间围绕前医师的离开和“我”选择去还是留展开,而在一次次与朋城的对话中,一件件事逐渐勾勒丰富了这个孩子的形象、心理世界以及惧学的成因。
开始见到朋城母亲的时候她就处于一种接近病态的方式,先是颤抖的表达对孩子的担心,突然转折表达将孩子托付给医师自己不常来,让人有些难以琢磨(莫名代入日剧mother中母亲的神情,还有绝叫最后的自白)。她时常给孩子灌输“只有妈妈会关心你”的想法,但却总以一种冒犯的行为去施加强制的爱。这是一种极强的控制欲。暴力的爸爸更让孩子的成长雪上加霜,其实孩子畏惧学校,有很大原因是那次接近失聪的暴打。“啊,快动手了”朋城把一切都压缩到盒子里,放到内心的墙角。【这里补一段话放到最后】朋城能精确的表述自己的想法,他说也许自己害怕的不是学校而是自己心底的什么,它本身就让人害怕,里面却可能什么都没有。在他们所谓的班级中,默默形成了不问来头的准则,而面对自杀的同学也像没发生过一样,是冷漠吗?是习惯了吗?或是什么呢?其实网络这一屏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些儿童的救命稻草,毕竟不是谁都有幸遇到像蔡医师这样的人。
蔡伯鑫作者本人作为儿童精神科医师,他对待朋城“我听你说”的方式完全符合我的理念,像我在《遥远星球的孩子》《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对自闭、抑郁的孩子的认知一样,“很多人都觉得这里的孩子只是在逃避,每个人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到来,但都讨厌自己也讨厌被恐惧困住的自己”。
最后忍不住再说一下自己吧,大概没人能看见吧。我的记忆一直不是很清晰,甚至初高中常常混在一起,我一直都是早上起很早吃早饭然后坐校车去上学的,大概是初高中交界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作业没写完还是怎么,也确实头痛犯了(据医生说是有神经性头痛,拍片也没有检查到有什么异常,而且是不定时、不定程度的头痛,最痛到站不起身),就逃过了上学尤其是早上的交作业,我似乎是尝到了甜头,于是每次头疼并不是很重的时候也会赖床不起(当然我从前起床从不赖床的),有时候会选择下午去,有时候干脆混过一整天。我有一个表妹,比较烦人聒噪那种,我又不太能忍受无端生事于是总会吵打,她爸爸就会打我,藏在竖在墙角的床垫后,藏在门后无果,我就总喜欢哭的特别大声,是真的声嘶力竭那种,写到这里我向左瞥了一眼那个伤痕累累的门,玻璃早已被打碎不知几次,只剩一块塑料板、斑驳木框、以及破碎但贴上卡通贴纸的门,我想我的头痛可能与此有关吧。【其实我很多症状以及思想状态都与抑郁症相似,我曾有一个朋友资讯过心理医生,其实他就和做出另一个选择的我一模一样。我能正常的与人交流,能压制自己的“病症”,能够帮助一些人好一些,也因此我很厌恶网络上有这么多自称抑郁症的人自杀,将一些不好的东西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