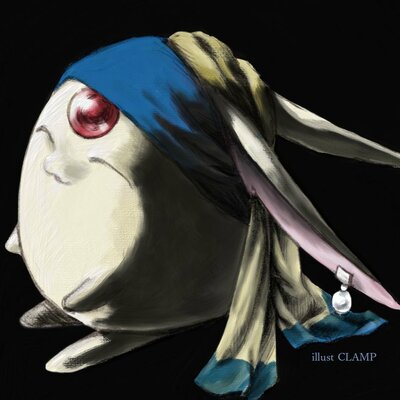01.01-01.05
01.02
在想黄金(和亮晶晶的东西)是否也是糖一样是人类的天然癖好,并正在被文化性的实践和社会经验加强呢?禾木科的甘蔗有六种,热带的最甜,种植它需要大量人力,因此是劳动密集型,也就和奴隶贩卖牵扯上了关系。一件并不那么神奇的事情是原本廉价的蜂蜜在制糖业已经发展完备的如今价格却逐步攀升已经超过了糖吧。 首先是阿拉伯征服南欧带去了蔗糖和一系列作物,制糖业的中心也在地中海,十六世纪随着殖民转移到北非与美洲大陆,先是神父再是国家(或者说官员)发现了殖民地(和茨威格的巴西联系在了一起),之后继续随着殖民转移到了大西洋岛屿上。十九世纪末期奴隶制的废除让制糖业继续发展并未之后资本主义的形成铺路。
01.03 糖的用途有五种:药品,香料,装饰,调味和防腐剂。从香料到调味伴随着其从稀少昂贵至普遍的过程。早期水果与肉的搭配也在糖上体现(比如肉末布丁和捣碎后拌在一起的菜,那时人们多用香料完全覆盖食物的味道……),这与中东的饮食习惯有一定联系。
从当时糖大多是与番红花、胡椒、丁香等香料共同出现以及购买数量可以推断其更多是作为香料使用(祭祀时用香料让人想到亚历山大用掉的那些,此书中也说这种做法来源于腓尼基人)。同时,糖与阿拉伯树胶/杏仁糊的混合液极为流行,塑性并凝固可当摆设,是权贵的象征。
01.04
蔗糖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无法大量享用它的阶层也渴望着糖。咖啡、酒、茶:巧克力、糖、面包,这些东西既是替代又能互补。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结束,需求与消费是过程和结果。下午茶出现,最初是女性的天地,尔后男性则抛下酒进入,劳动阶级并不能完全效仿。工业的发展让女性得以工作,果酱和面包一类即食物的消费增加。糖和肉分别被赋予给女性孩子和男性。
完读,如下是摘录。
我将考察大不列颠糖的消费历史,尤其是考察从糖开始变得相当普及的17世纪50年代,到它毫无疑问地成为每一个工人家庭的日常食物的20世纪初这段时间。
在美国,研究婴儿的学者们认为人类对甜味有一种内在的喜好,这种喜好出现在“人类发育的初期,而且相对地独立于外在经验”。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跨文化材料来支持这一论点,但是甜味似乎确实异常广泛地为人们所喜爱,以至于很难避免去推想这是人的天性。营养学家诺治·杰尔姆(Norge Jerome)所搜集到的材料显示,在世界不同地区,富含蔗糖的食物是如何参与塑造了非西方民族早期文化的传播适应经历;而在这些食物的传播适应过程中,则很少或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抗拒。大概值得一提的是,糖以及含糖食物的传播通常是伴随着刺激品,尤其是刺激性饮品。
在新食用者习得新食物方面,背后可能真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起作用:迄今为止,没有资料显示任何没有食糖传统的人类群体抗拒糖、甜炼乳、甜味饮料、蜜饯、糕点、糖果,或是其他甜味食物被引入其文化之中。
自1492年以来这个地区便处于帝国控制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这一帝国由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马德里以及其他欧洲和北美的世界权力的中心交织而成。一直到16世纪晚期,当新大陆殖民地的蔗糖生产居于支配地位之后,该地区的蔗糖生产才趋于终结。
大西洋诸岛是制糖业从旧世界迈向新世界的垫脚石,新世界的制糖业的原型便是在这些岛上得以完善的。
蔗糖在欧洲的价格已经飙升到足够支付长途运输的开销,这激发了更多在蔗糖生产上的冒险投入,特别是在西班牙所建立的加勒比殖民地,因为那里除蔗糖之外的商机(如采矿之类)正在严重地萎缩。
英格兰制糖业的开始
在自己的殖民地能够生产蔗糖以前,劫掠是英格兰获取蔗糖的不二法门。1591年一个西班牙间谍的报告中提到:“英格兰在西印度(指美洲)掠夺的战利品数量巨大,以至于蔗糖在伦敦的价格比在里斯本或者西印度群岛当地还要便宜。”
自从英国建立起第一个能够成功地向宗主国中心城市输出一些半成品商品(尤其是糖)的殖民地开始,皇室便通过法律来控制这些商品的物流及交易。
英国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毫无疑问是当时的大业主:一种大概多达百人的“农夫与制造工的混合”才可以在80英亩的土地上种植甘蔗,进而有望在收获季之后生产出80吨的蔗糖。要生产蔗糖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榨汁磨坊,一个提纯和凝缩蔗汁的蒸煮间,一个用来使粗糖脱水并使糖条干燥的烘烤间,一个制作甜酒的蒸馏间,同时还有一个装船前存放粗糖的贮藏间——所有这些意味着成千英磅的投资。
加勒比地区的“契约”佣工制结束于19世纪70年代,这种形式的佣工制开始时曾力图通过进口劳工这样的新措施来缓解废奴运动所带来的压力,并平抑劳动力的价格。在1876年时的波多黎各和1884年的古巴,奴隶制被废止。从此之后加勒比地区的劳工们(除了少数例外)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加勒比奴隶和欧洲自由工人间的联系既是生产上的,同时也是消费上的,促成这一联系的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而他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两个群体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没有其他更多对生产的投入;两者都从事生产,但却很少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两者也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在一些权威看来,他们实际是代表了同一个群体,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委身于别人为他们创造出的世界性劳动分工之中。
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量新的需求被激发出来——该需求是由骤然产生的低价所引发的,当时这些英国种植园生产的商货促成了同类商品价格的滑落,进而把英国中产阶级和穷人们引向了各种新奇的消费习惯。这样的需求一经成为现实,便很难再因为之后价格的涨落而受到动摇,该需求也迅速地蔓延至全国。
同样重要的还有英国人所经营商品的廉价化。“在这一层面”,他说,这一扩张过程“与一个世纪后所开启的技术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了人们消费由机器制造的便宜货的新习惯”。
茶面包黄油果酱
有趣的是三种几乎同时在不列颠广为人知的糙苦饮品——茶、咖啡和巧克力,在之前它们所处的文化环境里却没有一个会与特定的甜剂被一起饮用,直到今天中国人及海外华人喝茶时也都不加糖。——不过在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它深深受到英国输入的习惯的影响,同时也只是在英国的刺激之下饮茶才在印度普及。咖啡经常混着糖一起饮用,但并不是到处都如此,也并非向来如此,即便是在古代饮用咖啡的地区如北非和中东,也都没有加糖的习惯。巧克力在它热带美洲的老家,通常(并非一成不变)是作为一种不加甜剂的食物调料或酱汁。换句话说,茶、咖啡和巧克力有着诸多竞争对手,而糖却几乎是所有这些饮料的生产和消费所必需的。
而茶叶能够胜过其他苦味的咖啡因饮料,一则因为它食用起来更经济,而且不会完全散失其味道;二则因为它的价格在18世纪和19世纪时以相当稳定的速度下降,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于19世纪30年代被打破以后尤其如此;三则与第二条相关,茶叶开始在英国殖民地本土生产了。此外,通过税收,茶叶成为政府一项巨大的收入来源——到19世纪40年代,即使最便宜的中国波比茶(bobea),也被课以400%的重税。
然而自从与东印度的贸易开始以后……茶的价格……变得很低,以致最贫贱的劳动者也能够消费得起——就在同一时期,苏格兰的很多商人凭借在戈腾堡(Gottenburg)的瑞典公司效力的同胞的关系,引入了这一刺激物,成为底层人民的日常消费品;也在同一时期,曾几何时还是稀有品的糖,作为茶不可或缺的伴侣......
一旦把一种不含酒精、苦味的、缺乏热量而有刺激性、燥热的液体饮品与一种富含热量、有强烈甜味的物质混合到一起,这便意味着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饮料组合。
无论在欧洲哪个国家,普通百姓居然不得不把从地球上遥远的两端所进口的两种物品当作他们的日常饮食,这都是非常奇怪的事。然而,庞大的战争开销以及国际局势的瞬息万变所导致的高税收,妨碍了王国内的穷苦人民去食用这片土地上出产的天然产品,并迫使他们去依赖于那些舶来品。可以肯定这并非他们自身的过错。
在19世纪的苏格兰,永佃农(称作hinds)的收入有2/3是以实物(包括食物)方式支付的。这些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吃得比那些打临工的农业劳动者要好
黄麻纤维工业为女性劳动者提供了机遇,于是邓迪的许多家庭主妇都开始出外工作。“当母亲有工作时,到‘吃饭时间’她就没空来准备麦片粥或肉汤……通常早餐和正餐就变成了面包和黄油。而学校下课让学生去用餐的时间与工厂的‘吃饭时间’并不一致,于是小孩只好自己回家找点吃的……” 家庭主妇在时间上的压力本身就足以解释选择次等饮食的原因。
白面包虽然和肉、黄油和乳酪一起吃起来更香,但也可以不要这些,只要一杯茶就可以把冷饭变成热食,并给人以舒适和惬意的感觉。19世纪中期时6先令或者8先令一磅的茶仍然是奢侈品,但以一个工人家庭的平均消费量——一周2盎司,通常还要点缀几片烤面包——来看还算不上奢侈。这类饮食在早期的工业背景下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们随手可得而且无需花费时间来烹制。
他们在1905年最大并且利润最高的市场是在劳动阶层中;对于这个阶层,曾几何时作为奢侈品的果酱现在成为了一种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更为昂贵的黄油的替代物。
如下的观察解释了19世纪工人阶级日常饮食中糖和肉类消费的表面增长:“面包是穷人的主要食物,如果人们能够买得起肉食,吃得起那些配着糖吃的菜肴,他们便很少吃面包。”
从19世纪50年代起,茶和蔗糖的消费量就开始稳步攀升,
蔗糖的功效和消费
自然界里被称为碳水化合物的一族,是由碳、氢和氧所构成,其中包括了糖,而蔗糖则是糖中最重要的一种。它可以在所有植物的草叶里,在植物根茎中,以及一些树木的树液中被找到。在光合作用下,二氧化碳和水的混合制造出了蔗糖、淀粉和其他种类的糖。人体不能产生糖而只能消耗糖。通过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在吸收氧气的同时,葡萄糖(血糖)被转化为能量,同时二氧化碳被排出体外,“糖的食用因此成了与糖的形成相反的过程”。
“没有一个处方里会少了糖,给穷人的药方里它也被列了进去,作为昂贵的干糖药剂、宝石和珍珠的替代品——后者只属于富人的药方。”
在1700年以前的英格兰,蔗糖的非药用消费除了装饰和防腐外,主要有三种形式:香料和糖果;甜的酒精饮料;经烘焙加工而成的甜味食品。
在英国,蔗糖消费的性质和规模到1850年时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蔗糖的流行最早不过是始于1650年,1650年以后蔗糖的价格开始下跌而数量激增,越来越多的人伴着茶一起(或者是与一种其他的新饮料混合)品尝到糖。蔗糖向社会下层的传播缓慢而曲折,但一直持续着;而仅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蔗糖就辗转到了最贫困者的手中。
在1700年早些时候,传播的速度开始加快。对于那些新的食用者来说,正如我们所见,蔗糖开始在日常饮食中扮演起全然不同的角色来。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占取更多殖民地,建立更多种植园,输入更多奴隶,修建更多船只,进口更多糖和其他种植园产品,所有这些也都着实被推动了起来。
到之后的1750—1850年之间,蔗糖已不再作为奢侈品而成为一种必需品。1750年之后,酥皮糕点、布丁、果酱面包、糖蜜布丁、饼干、果馅饼、小圆面包和糖果越来越多地现身于英国人的日常饮食中,而到1850年以后更是泛滥成灾。在这以后,更胜一筹的制糖甜菜的生产与热带甘蔗生产地之间的竞争,毫无疑问使得歧视性关税逐步走向消亡。
19世纪晚期,甜品成为一道固定的菜。加糖的浓缩牛奶最终成了茶和水果羹的伴随物“乳酪”,商店里卖的甜饼干成了喝茶时的一大特色,而茶则成了所有阶层表示好客之道的标志。
同在19世纪末,面包开始受到其他食物的排挤,以后这一过程在许多其他国家也一再上演。
*
英国的蔗糖使用史揭示了两个基本的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降,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从大约1850年以来,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在1750—1850年的岁月里,无论多么孤独穷困,也无论什么性别年龄的英国人都领教到了糖,而且绝大多数人对糖的喜好发展到愿意超出负担能力去消费它的地步。1850年以后,当蔗糖价格骤降时,这一嗜好终于可以实现;糖也从1650年的稀有品、1750年的奢侈物,转变为1850年的生活必需品。 此外似乎可以肯定,尤其在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成了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糖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中的地位,1850年和1750年相比有着质的区别。造成区别的原因,是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该经济与海外殖民地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尤其在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成了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糖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中的地位,1850年和1750年相比有着质的区别。造成区别的原因,是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该经济与海外殖民地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食物技术主义者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因为浓稠的液体要比白水更能满足人们的口感。“口感”一词用来描述的是对软饮料这样的液体“质感”的感受,糖可以使得这样的质感更饱满或是更加恰到好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批术语与味道没有什么关系:真正有关的是“质感”或“口感”,而不是味道。就如同蔗糖使得软饮料喝起来“更浓郁”一般......
豆知识
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埃及的制糖技术,随着征服的结束而在地中海地区传播开来。许多重要的作物,如稻、黍、硬质小麦、棉花、茄子、柑橘类水果、香蕉、芒果和甘蔗都是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而得以传播的。
“塔瓦阿撒卡”的意思是榨糖磨,它位于距离杰里柯城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其遗址留存至今。
奴隶的解放(丹麦在1848年,英格兰在1834—1838年,法国在1848年,荷兰在1863年,波多黎各在1873—1876年,古巴在1884年)
伦敦第一家咖啡店是1652年由一个土耳其商人最先经营起来的,之后它以令人讶异的速度风靡欧洲大陆和英格兰。
17世纪晚期,在上流社会,一餐饭的末尾为客人们分配甜点才作为惯例而固定下来。
一个“布丁”差不多总是意味着以面粉、动物油脂、干果、糖以及添加的鸡蛋作为主要成分,
14世纪王室厨师们的“糖梨”最终变成了19世纪的蒂普崔(Tiptree)、凯勒(Keiller)、克洛斯和布莱克威尔(Crosse and Blackwell)、奇弗斯(Chivers)等罐头生产商所生产的果酱和橙子酱。
1425年左右,啤酒花开始添加到淡啤中,主要是用于对饮料的保质——这时基本上可以称为啤酒了——但同时味道也变苦了
第一个贸易三角:工业制品被运往非洲,非洲奴隶则被贩到美洲,而美洲的热带商品(特别是蔗糖)则销往宗主国及其重要邻国。第二个贸易三角(发挥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和重商主义者的理想有些矛盾):从新英格兰把朗姆甜酒运到非洲,同时把奴隶贩到美洲,以及把糖蜜运回新英格兰(以此来制作甜酒)——第二个贸易三角的成熟使得新英格兰殖民地与英国之间产生了政治上的摩擦,这背后实际是经济问题,之所以上升到政治层面更确切来说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利益分歧。
奴隶劳动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联的劳动力模式之间是如此矛盾,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被视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
随着蔗糖日益深入到某些消费形式所构成的整套“礼仪体系”(the ceremonial nexus)。
米徳倾向于认为,甜食在英国人饮食实践中的出现是出于对法国的效仿。鉴于英国王室的许多习惯都来自法国宫廷,所以这确有可能。
糖雕的制作技术和各种仪式的使用方法,大概是经由意大利、法国,从北非向北欧传播的。
就在英国人的兴趣从啤酒和淡啤转向杜松子酒和朗姆酒,之后一部分人又返回到啤酒和淡啤之上的同时,他们学会了喝甜味很重的茶(这一爱好意义深远);法国人自始至终主要嗜好的却还是葡萄酒。在17世纪时法国人学会了喝咖啡,虽然这一点很重要——米什莱(Michelet)甚至相信法国大革命的兴起部分是受到了喝咖啡的影响,然而咖啡却没有让法国人少喝葡萄酒。
般情况下,加工1吨的甘蔗需要500公斤的蒸汽,每吨潮甘蔗渣则可以产生2.3吨的蒸汽。
伴随发展的过程,蔗糖在预加工食物中使用的比例越来高。
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越是发达的国家,蔗糖的非家庭的工业式消费所占比例越高越高。
只是在独立革命之后,美国人才逐渐放弃了糖蜜、朗姆酒和茶,取而代之以枫糖、玉米糖、威士忌和咖啡。
评价
然而,不问意义是如何注入行为的,只关注结果而忽视过程,则是对历史的一再漠视。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产物,还是一种产生过程;不光是被社会所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正如解码针对的是整个编码过程,而不单是密码本身。
自从人类开始将摄食和禁食视为达至健康和纯洁的手段以来,食物和药物就在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中联系在了一起,而糖成为“食物”和“药物”的联结桥梁,已有上千年之久。
为什么北方比南方的人们对甜味有着更为热切的渴望:即使在现代社会,经过加工后的蔗糖,依然主要是北方的人口拥有最高的消费比。而在从中国南方到印度、波斯和北非的广大亚热带地区,人们食糖的历史早在欧洲人对糖有所了解之前就已经开始;而威尼斯人第一次接触糖就被它迷住,时间则不迟于10世纪。
预制食物是与人们越来越多地不在家里、不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情况同步出现的。这样的变化趋势确实给了人们选择食物的自由,从而使消费者免于一道道的上菜过程,也告别了家庭餐桌旁的社会交流,摆脱了模式化的餐饮方式和
都没有好处的事物之上。各种观点各执一端,一些人倾向于支持扩张诸如糖之类商品的消费,其主张的依据是认为消费扩张对于消费者和国家都是一件好事;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反对这种扩张,反对的依据是消费扩张在生理和伦理上会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
那些有助于增长消费者基于其自身(他或她)购买力的“权利”的消费行为,为了这些消费行为而进行的抗争,与更多“进步”资本家们扩大市场和利润的欲望步调一致。虽
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已准备改变立场(他们也经常那么做了)。然而他们表面上变幻莫测的立场,并未减弱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影响的权力。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能够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借助这样的条件英国举国上下都能够享用到数量不断增长的蔗糖及类似的商品。这样的影响力具体表现为,主动针对一般税种和关税设立特定的法律;通过政府代理来分配蔗糖、糖蜜和甜酒的供应,例如在海军和公立救济院中的供应;或者通过规范来控制糖的纯度和质量标准等。不过,这些影响力也涉及一些非正式的权力运作:借助党派、家族关系,大学和公共学校裙带关系,暗箱操作,联谊会、俱乐部,用钱来疏通关系、用职位来贿赂,花言巧语的诱骗以及其他种种高压手段和官方特权的混合,这些花样中的大多数对于任何一个当今报纸的严肃读者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了。
些用途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下和向外“顺延”的社会上层的用途(包括其中的一些意义);另一类是与“顺延”相对,更多属于独立创新的用途。在这两条不同发展路线的结合点上,暴露出了权力与“内在意义”的关系。
把过程与特定时代相分离的做法,就像把糖的消费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一样,只会把讨论局限在一点上;要解释事物为什么会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样子,这得取决于一个社会系统中各组成部分里既存的各种关系。而回顾历史能使我们看清上述这些关系是如何逐渐成形的。
即便如上面所述,我们的思考又该何去何从?为什么英国人变成了狂热的蔗糖消费者?不是因为人类天生对甜味的嗜好;不是因为我们人类是以符号来交流,从而把包括吃在内的所有事物都赋予意义;不是因为等级较低的人社会性地效颦等级较高者;甚至不是因为居住在寒冷、潮湿气候里的人们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喜欢糖。越平常的事实似乎越有说服力。不列颠工人们的日常饮食既缺乏热量又营养单调。劳动者们时常吃不上热食,特别是在他们的早餐和午餐时。新的工作与休憩时间安排,雇佣条件的变化,农业劳动者与乡绅之间依附关系的终结,生产体系以及在这之后工厂系统的发展——这些都位列于饮食习惯变革的背景性条件之中。基于它们,才有所谓人们力图效仿地位优越者的攀比之心,进而拓宽了解释的基础。当我们再读到那些对糖的溢美之词,并回想起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迅速向城市化迈进、更有时间意识、具有工业化特点的社会时,我们便不会惊讶:斯莱尔所说的听起来倒是比汉韦更接近真相
先前我已经提出了习得和实现“内在意义”的两种过程。在“顺延”中,一群人复制、模仿甚至是竞争性地仿效着另一群人的消费实践,而这另一群人通常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以雕花装饰,配上“糖丸”、贺词和硬糖塑像的婚礼蛋糕,这样的蛋糕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新的“食物”;消费牢牢地嵌入到了特定的场合之中,它被仪式化为这些场合的一部分。当食用婚礼蛋糕这一习俗向下传遍整个社会之后,由于条件和环境方面的极大差异,可以预料的是蛋糕的用途会发生改变。即便如此,“仿效”依然是这一习俗流传的关键所在,所以这整个过程是一种“顺延”
但是,即便承认人类赋予了客观世界以意义,而且不同的人类群体有不同的意义体系;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在特定的历史场合中,意义的赋予究竟是由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达成的?意义究竟栖居在何处?多数时候,对于大多数的人类而言,意义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而意义被相信是内在于事物之中,内在于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人们的行动中。我们中大多数人,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行动的剧本在很久以前已被写就,剧本中的形象需要的是认同而不是创作。这样说并非要否定个体性或人类所具有的添加、转换和拒绝意义的能力。不过仍然要强调的是,我们作为个体所编织的意义之网,都过于袖珍而精致(且非常琐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同时也栖息在其他规模庞大的意义之网中,这些意义之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凌驾于个体生活之上。
一些人倾向于支持扩张诸如糖之类商品的消费,其主张的依据是认为消费扩张对于消费者和国家都是一件好事;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反对这种扩张,反对的依据是消费扩张在生理和伦理上会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并且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长时间以来,那些有助于增长消费者基于其自身(他或她)购买力的“权利”的消费行为,为了这些消费行为而进行的抗争,与更多“进步”资本家们扩大市场和利润的欲望步调一致。虽然在一些个例中情况并非如此——例如酒精饮料,因为它会妨害到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茶、蔗糖和类似刺激品的例子中,上述情形的确存在。
一这些变化都与“外在意义”相关——蔗糖在殖民地历史、商业活动、政治阴谋以及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的地位——这些又都与“内在意义”相互关联。说这些变化都与“外在意义”相关,这是因为人们所赋予的蔗糖的意义,它们得以兴起的环境更多是由提供蔗糖的人所决定的,而不是消费者。在英格兰,富豪权贵们最早吃上糖并赋予其新意义之前,他们首先必须得到它。之后当蔗糖变得更加普通和为人所熟知时,它的食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不难设想的是,透过食用形式所传递的意义其中一些是新发明,而另一些则是综合了各处学来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社会群体将行动、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化成了不同的意义单元。仪式联系着进食,例如仪式总是与一些特别的食物有关(要么是属于禁忌,要么是符合传统或规制);或者在仪式情境中,普通食物的意义变得不同寻常起来。上面说的两种情况,具体例子很多,例如逾越节家宴、圣餐、感恩节的火鸡等。而通过吃特定的食物来表示一个时间单元(“星期”)的结束,或表示一个休息的日子,这样的习俗广为流传。
饮食本身恰恰是社会性的,其中牵扯到交流、给予和索取、寻求一致性、个人的基本需求、通过照顾到别人的需求来妥协。社会互动为人们意见的表达以及群体内部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然而有人却视这些为加诸个人自由之上的束缚。
这样的一些变迁使得人们的饮食变得愈加个人化并缺少互动性——成了“去社会性”的饮食。饮食方面的选择(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吃什么、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不再关乎一起吃饭的伙伴,而是一方面受制于食品生产加工技术所决定的食品范围,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人们当下实际感受到的时间束缚。
那些劝说人们追逐“现代”、“高效”、“时髦”以及“个性化”,工于心计的鼓噪变得愈加老练。我们吃什么我们便是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所是”越来越被弄成了我们的“所吃”,无论何时那些我们无力支配的力量总是在劝说我们,我们的消费联系着我们的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