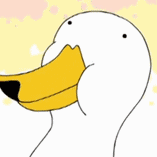熟悉的套路,误导性满满的结论……
真正的智慧的不可见性和可见之物的不可认识性,西方形而上学在柏拉图那里就将认识对象分裂为真理和美,也将人类伦理的目的分裂为认识和快感。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试图用想象力将美学驱逐出科学的领域,品味既是知识(快感的溢出)又不是知识(表征相对于知识的溢出),品味成了一个物自体,这只能陷入二律背反的否定性。柏拉图在《会饮》里试图用爱欲来统一知识和美,爱是对美的欲求(斐多),也是对知识之爱(苏格拉底),然而爱欲έεος,丰饶神和贫乏神之子,它不是神而只是δαιμον,和φιλοσοφία意义都属于中间之物,如阿甘本所说,和品味一样,是主体之人形成过程的门槛。按照阿甘本对几位古典大师的分析,品味不过是溢出的能指,美的概念不过是个缺乏所指的纯粹能指,有如星丛一般只能被接近而不能被认识。由于美,溢出的能指得到了配置,由于爱,观念中的现象得以被保存。柏拉图的知识型的分裂被阿甘本对应于本维尼斯特对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分裂,现代科学的发展将占卜知识/不可知的知识排除出去,只留下越来越多的溢出的能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交换价值上,这是一种我们无法享用的快感,它同样是个纯粹能指。精神分析中的那种未知的知识(潜意识),也是一种纯粹能指。科学越发展,溢出的能指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将人界定为“会说话的有理性的人”开始,人就处于意指关系和知识的断裂之间,启蒙以来的哲学家的唯一的知识主体的人不过是天真的构想,即便是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启蒙的反叛也不过只是把问题变成了作为知识主体的大他者和认识主体之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符号学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能指和所指的统一,弥补二者之间的裂缝。最后阿甘本要求回到爱-智慧(哲学)中去,它本然地处于裂缝之中,唯有它才能“在纯粹表象中保存现象”,“哲学意味着美必须保存真理,真理必须保存美。在这个双重保存中,知识得到了实现”。“唯有如此快乐和科学才能统一起来,才能赢得智慧的理想,也就是品味。”
这结论着实可疑,知识分裂的解决之路在分裂之处,只需把不可言说和不可认识之物(存在和看不见的真理)交给作为溢出能指的占卜,占卜难道不是不可认识的科学,是纯粹偶然性的么?我以为您老要批判西方形而上学这种根源的分裂性和知识的不可靠性呢。是您老的误导性太强了么……老套路,总是要借助中介之物。
附录 1 分析本维尼斯特的《词语与声音》很精彩,可以窥见阿甘本一直以来对语音的哲学构想,那些发音指示词不过是空能指,仅仅指示话语的状态,言说的声音不过标示着“言说”这件事的发生,即声音的出现,言说者首先是个声音,而写作将语音从语言中抹除了,因为写作事先地被包含在文字的符号中。在阿甘本看来,本维尼斯特用 voice 去跨越裂缝的尝试是失败的。但问题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已批判过语音中心主义(实质是λογος中心主义,理性主义),此处看不出阿甘本较之德里达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