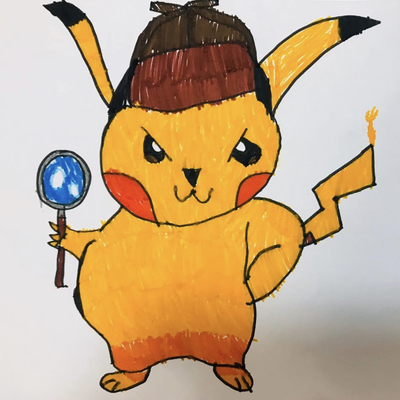一点记录
@2020-05-25 15:10:05 1. “59-婆罗浮屠佛陀头像”-P346: “我一向认为,宏伟的宗教建筑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矛盾,而参观婆罗浮屠让我对这一观点有了前所未有的感触:修建这样一座建筑需要大量的物力,需要深涉种种俗世事务,但修建目的却是要启发我们放弃身外之物、与世无争。” 《空间的敦煌》中,巫鸿有段文字介绍“法供养”的概念:“……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莫高窟中经变画的流行很可能直接受到大乘佛典中特别推崇的“法供养”的影响。据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法供养者,诸佛所说深经……十方三世诸佛所说,若闻如是等经,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故,是名法之供养。”这种供养比任何其他类型的供养,如衣服卧具、香花幡盖、修行戒行等,都要重要和深刻,同一《维摩诘所说经》因此反复强调“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为最,第一无比”。[38)从这个角度看,此窟和莫高窟中的许多经变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向朝拜者解释佛经(实际上在幽暗的洞室中很难看清这些图画),而在于以图经的形式实践这种最高水平的对佛供养。”。我很认同巫鸿的见解,修建宗教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虔诚的宗教实践活动,修建的目的和修建的活动并无冲突。
本书一直强调文物对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我认为,民族认同本身就是一个有毒的概念。对本民族的认同极易演化成对其他民族的不认同,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二十世纪最大的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在德国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时至今日,种族灭绝,作为文明的疮疤,旧伤尚未愈,新伤复又来,笼罩在头顶的恐怖阴影从未散去。作者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上,本意是好心的提醒西方文明应该尊重世界上其它同样璀璨的文明成就,然而,鼓吹民族认同所产生的副作用是需要保持最高警惕的。
世界各地的人,在基因层面,都是传承自远古智人,并无不同;社会生活方面,各种生活用品和食材也由连接世界的贸易网络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思想文化上,各种文明通过教育和出版系统对全人类开放和共享。世界大同的物理条件已经具备,何处何从,取决于个人心理上的选择。所以,人只要走出自己内心划下的牢笼,去了解别人,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基于虚浮的偏见划分我者和他者互相攻伐,这个世界是会好起来的。一念为善,一念为恶,琐罗亚斯特所描绘的善恶交战的战场,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每一个念头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