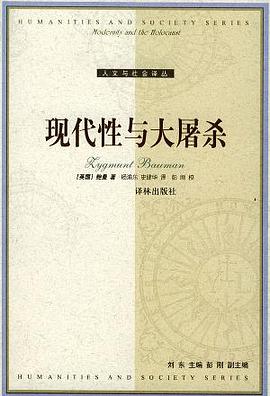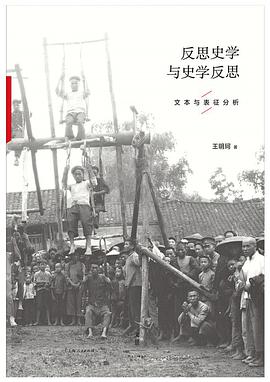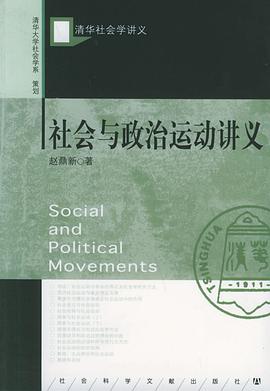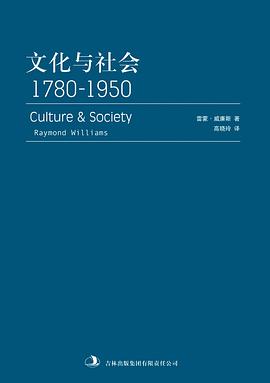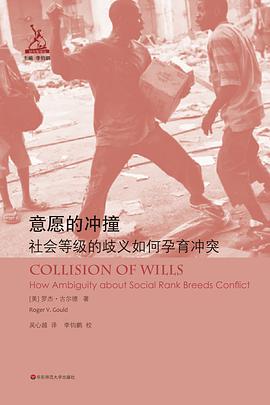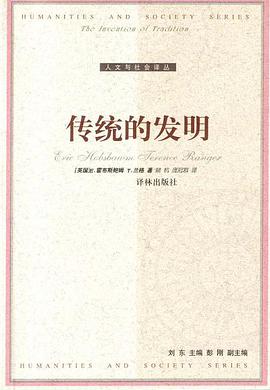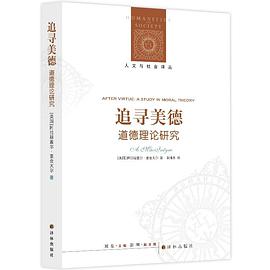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L.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G.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p.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