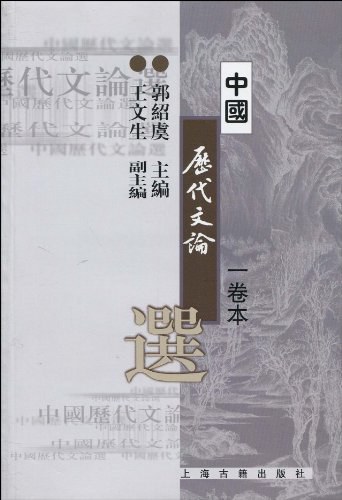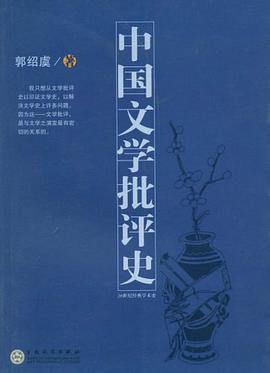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 豆瓣
作者:
郭绍虞
/
王文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1
尚书・尧典〔节录〕
帝①曰:夔(2)!命女典乐(3),教胄子(4)。直而温(5),宽而栗(6),刚而无虐(7),简而无傲(8).诗言志(9),歌永言(10),声依永(11),律和声(12)。八音克谐(13),无相夺伦(14),神人以和(15)。夔曰:於(16)!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7)。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注释】(1)帝:指舜。(2)夔:人名,相传是尧舜时掌管音乐的人。(3)女:汝,你。 典光:主管音乐。(4)教胄子:胄,长。这句谓教育子弟,使其成长。一说,胄子指嫡长子。《史记・五帝本纪》作《教子》。(5)直而温:正直而温和。(6)宽而栗:宽弘而庄严。栗,坚貌。(7)刚而无虐:刚毅而不苛刻。无,不,下句同。(8)简而无傲:简易而不傲慢。(9)诗言志: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史记・五帝本纪》作“诗言意”。(10)歌永言:永,长。这句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11)声依永:谓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声,五声,宫、商、角、徵、羽。(12)律和声:谓律吕用来调和歌声。律吕,六律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13)八音:《周礼・春官・大师》: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里金指铜钟,石指石磬,木指木制的祝(音祝,形如漆桶)、(音语,形如伏虎),大抵都属体鸣器;革指鼓,属皮乐器;竹指帘,匏(葫芦之属,古代制笙的材料)指笙,属气乐器;土指埙(音勋,陶哨),兼涉于体鸣乐器和气乐器。这是八音的原始分类法。后来因乐器所用的材料逐渐复杂,分类也好生变化。八类乐器不同,所发的音也不同,所以称为八音。 克谐??达到和谐。(14)无相夺伦:不要搅乱次序。 无,毋。(15)神人以和:原书以为神和人通过诗歌音乐可以交流思想感情而能协调和谐。(16)於:音乌,叹词。(17)击石拊石二句:石,磬。拊,小击。二句旧注谓击附石磬,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按:百兽率舞疑为原始社会的图腾舞。百兽指各种化装的动物图腾。
【说明】 《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相传由伏生口授,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尧典》为其中的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把下半篇分出,并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 这里节录的一段文字,记载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长久的影响。由于“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影响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时,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
帝①曰:夔(2)!命女典乐(3),教胄子(4)。直而温(5),宽而栗(6),刚而无虐(7),简而无傲(8).诗言志(9),歌永言(10),声依永(11),律和声(12)。八音克谐(13),无相夺伦(14),神人以和(15)。夔曰:於(16)!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7)。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注释】(1)帝:指舜。(2)夔:人名,相传是尧舜时掌管音乐的人。(3)女:汝,你。 典光:主管音乐。(4)教胄子:胄,长。这句谓教育子弟,使其成长。一说,胄子指嫡长子。《史记・五帝本纪》作《教子》。(5)直而温:正直而温和。(6)宽而栗:宽弘而庄严。栗,坚貌。(7)刚而无虐:刚毅而不苛刻。无,不,下句同。(8)简而无傲:简易而不傲慢。(9)诗言志: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史记・五帝本纪》作“诗言意”。(10)歌永言:永,长。这句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11)声依永:谓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声,五声,宫、商、角、徵、羽。(12)律和声:谓律吕用来调和歌声。律吕,六律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13)八音:《周礼・春官・大师》: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里金指铜钟,石指石磬,木指木制的祝(音祝,形如漆桶)、(音语,形如伏虎),大抵都属体鸣器;革指鼓,属皮乐器;竹指帘,匏(葫芦之属,古代制笙的材料)指笙,属气乐器;土指埙(音勋,陶哨),兼涉于体鸣乐器和气乐器。这是八音的原始分类法。后来因乐器所用的材料逐渐复杂,分类也好生变化。八类乐器不同,所发的音也不同,所以称为八音。 克谐??达到和谐。(14)无相夺伦:不要搅乱次序。 无,毋。(15)神人以和:原书以为神和人通过诗歌音乐可以交流思想感情而能协调和谐。(16)於:音乌,叹词。(17)击石拊石二句:石,磬。拊,小击。二句旧注谓击附石磬,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按:百兽率舞疑为原始社会的图腾舞。百兽指各种化装的动物图腾。
【说明】 《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相传由伏生口授,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尧典》为其中的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把下半篇分出,并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 这里节录的一段文字,记载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长久的影响。由于“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影响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时,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