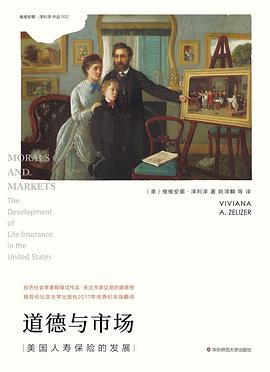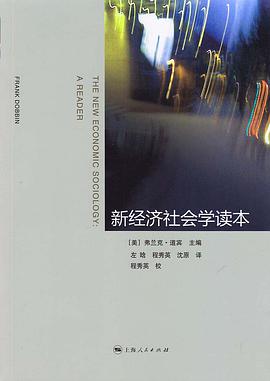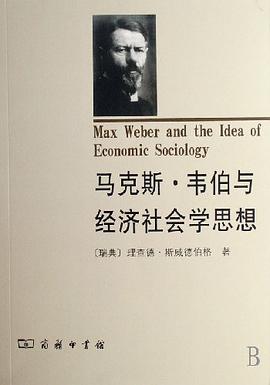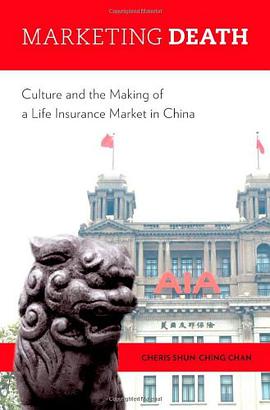道德与市场 豆瓣
Morals and Markets :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7.6 (5 个评分)
作者:
[美]维维安娜·泽利泽
译者:
姚泽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 6
《道德与市场》是杰出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的首部专著,此次也是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中文译本。本书自1979年首版后在近四十年间长盛不衰,最新修订版201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研究以人寿保险为例:曾在美国被斥为亵渎人类生命的赌博的人寿保险,最终是怎样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对家庭未来的可靠保障的?书中,泽利泽将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学视角结合起来,提出了对人寿保险行业的新颖阐释,开创了对于经济行动的道德以及新的经济行动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她为我们展示了与美国的工业革命同时进行的美国社会对于死亡、金钱、家庭关系、财产和个人遗产的观念的演进,提供了解答此类问题全新的分析手段。
-----------------------------------------------------------------------------------------------
专家推荐:
人寿保险看起来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一种产品,直到泽利泽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购买人寿保险现在被当作一种道德义务,但当我们得知这曾经竟是一种可耻的做法时,消费所蕴含的社会和符号意义的巨大转变让人望而生叹。这是一部突破性的著作,每一章都会给人丰厚的启示。
——马克·格兰诺维特,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嵌入理论和弱连接优势理论提出者
维维安娜·泽利泽革新了我们对于现代经济的思考。此前,波兰尼详细描述了英国精英怎样放弃了对农民的道义责任转而接受自由劳动市场,为历史提供全新注脚;泽利泽则展示了为什么所有新型市场的创造者都必须为其打下道德基础。《道德与市场》永远不会过时。
——弗兰克·多宾,哈佛大学教授,组织、经济行为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著名学者
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开创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对经济行动道德性的研究(亚当·斯密将其作为核心议题,但被他的追随者抛弃);以及新的经济规范的正常化和制度化;现在,美国正在道德层面就健康保险展开争论,全世界也忙于应对比特币以及其他私人货币的崛起。这项研究层面无可挑剔并且拥有惊人的洞察力的作品,在此时无疑极具现实意义。
——保罗·迪马乔,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新制度主义理论著名学者
在今天,这本书中的论点及其极富创造力的研究路径,同它1979年初版之时一样鲜活。同泽利泽所有作品一样,书中论点兼具社会学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
她的研究路径是一种巧妙而独特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兼顾了价值观和社会关系。这本《道德与市场》是一部难能可贵的经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康奈尔大学教授,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
本研究以人寿保险为例:曾在美国被斥为亵渎人类生命的赌博的人寿保险,最终是怎样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对家庭未来的可靠保障的?书中,泽利泽将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学视角结合起来,提出了对人寿保险行业的新颖阐释,开创了对于经济行动的道德以及新的经济行动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她为我们展示了与美国的工业革命同时进行的美国社会对于死亡、金钱、家庭关系、财产和个人遗产的观念的演进,提供了解答此类问题全新的分析手段。
-----------------------------------------------------------------------------------------------
专家推荐:
人寿保险看起来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一种产品,直到泽利泽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购买人寿保险现在被当作一种道德义务,但当我们得知这曾经竟是一种可耻的做法时,消费所蕴含的社会和符号意义的巨大转变让人望而生叹。这是一部突破性的著作,每一章都会给人丰厚的启示。
——马克·格兰诺维特,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嵌入理论和弱连接优势理论提出者
维维安娜·泽利泽革新了我们对于现代经济的思考。此前,波兰尼详细描述了英国精英怎样放弃了对农民的道义责任转而接受自由劳动市场,为历史提供全新注脚;泽利泽则展示了为什么所有新型市场的创造者都必须为其打下道德基础。《道德与市场》永远不会过时。
——弗兰克·多宾,哈佛大学教授,组织、经济行为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著名学者
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开创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对经济行动道德性的研究(亚当·斯密将其作为核心议题,但被他的追随者抛弃);以及新的经济规范的正常化和制度化;现在,美国正在道德层面就健康保险展开争论,全世界也忙于应对比特币以及其他私人货币的崛起。这项研究层面无可挑剔并且拥有惊人的洞察力的作品,在此时无疑极具现实意义。
——保罗·迪马乔,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新制度主义理论著名学者
在今天,这本书中的论点及其极富创造力的研究路径,同它1979年初版之时一样鲜活。同泽利泽所有作品一样,书中论点兼具社会学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
她的研究路径是一种巧妙而独特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兼顾了价值观和社会关系。这本《道德与市场》是一部难能可贵的经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康奈尔大学教授,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