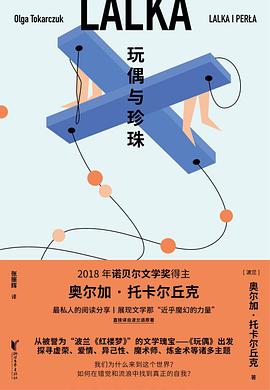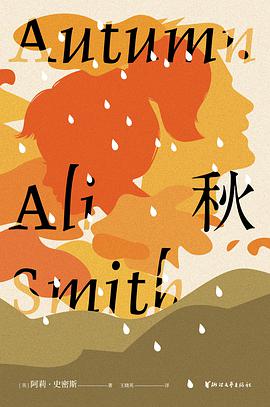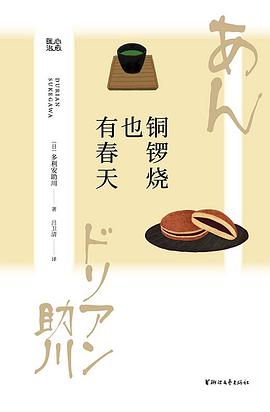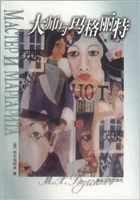玩偶与珍珠 豆瓣
Lalka i perła
8.0 (7 个评分)
作者:
[波兰]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译者:
张振辉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
- 6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zui私人的阅读分享;直接译自波兰语原著
▷从被誉为“波兰《红楼梦》”的文学瑰宝——《玩偶》出发
▷探寻虚荣、爱情、异己性、魔术师、炼金术等诸多主题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如何在错觉和流浪中找到真正的自我?答案都在这本书里
————————
【内容简介】
《玩偶与珍珠》是托卡尔丘克的一部分析波兰作家普鲁斯的长篇小说《玩偶》的散文作品。《玩偶》是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被誉为波兰的《红楼梦》。《珍珠颂》是由米沃什译为波兰文的一个童话,关于一位王子到民间寻宝而忘记自我的故事。
从《玩偶》与《珍珠颂》出发,托卡尔丘克向我们呈现了一堂文学大师的阅读课。探寻了虚荣、爱情、异己性、魔术师、炼金术等诸多主题。托卡尔丘克希望通过她的阅读图谱带领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如何在错觉和流浪中找到真正的自我?
————————
【媒体推荐】
“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
“她运用观照现实的新方法,糅合精深的写实与瞬间的虚幻,观察入微又纵情于神话,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具独创性的散文作家之一。她是位速写大师,捕捉那些在逃避日常生活的人。她写他人所不能写:‘世间那痛彻人心的陌生感。’……她的文风——激荡且富有思想——流溢于其大约十五部的作品中。”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讨论普鲁斯的小说《玩偶》的这部作品,证实了她自身也独具特色。托卡尔丘克可能是她的同代作家中,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了传统——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产生的问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精神社区——的人。书中讨论了科学与艺术,知识与形而上学,个体的内在自由与外在的历史的关系。但书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普鲁斯。托卡尔丘克怀着对老前辈的敬意,缓缓阅读着小说。”
——格拉齐亚·鲍尔库夫斯卡, 波兰文化期刊Res Publica Nova
“《玩偶与珍珠》证明了普鲁斯那部小说的伟大,也记录了托卡尔丘克结合自己的世界观和经历进行的一次私人阅读的体验。她认为《玩偶》是一部启蒙小说,描写了人们寻找,并且找到了生命意义的过程。”
——卡兹米尔茨·麦西格,波兰文艺期刊Fraza
“她以一种来自女性的、天然的细腻与温柔,同时以敏锐的目光,努力沉入万物内心,融为世界的一部分,然后替万物发声,替世界讲述。这是托卡尔丘克的不同之处,也正是她的不凡之处。”
——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教授 赵刚
“托卡尔丘克始终秉承着波兰多元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提出着可以引起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广泛共鸣的普遍问题。”
——波兰驻美国大使 彼得·维尔泽克
“托卡尔丘克跟随着自己的好奇心,大胆地前行,从不受困于种种边界和类型的藩篱。她笔下的人物都鲜活地存在于书页之间,他们发出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巴黎评论》
“在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她是欧洲最重要的人本主义作家之一,致力于欧洲大陆的思想和散文主义小说传统。”
“托卡尔丘克童年时便通过她对童话和神话的敏锐直觉,建构了她对万事万物——人、动物、植物、风景等——之间联系的理解,成为作家后的她试图通过想象力证明,童年时的好奇心并没有被成人社会粗暴地切断,依然在她的作品中延续。”
——《卫报》
▷从被誉为“波兰《红楼梦》”的文学瑰宝——《玩偶》出发
▷探寻虚荣、爱情、异己性、魔术师、炼金术等诸多主题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如何在错觉和流浪中找到真正的自我?答案都在这本书里
————————
【内容简介】
《玩偶与珍珠》是托卡尔丘克的一部分析波兰作家普鲁斯的长篇小说《玩偶》的散文作品。《玩偶》是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被誉为波兰的《红楼梦》。《珍珠颂》是由米沃什译为波兰文的一个童话,关于一位王子到民间寻宝而忘记自我的故事。
从《玩偶》与《珍珠颂》出发,托卡尔丘克向我们呈现了一堂文学大师的阅读课。探寻了虚荣、爱情、异己性、魔术师、炼金术等诸多主题。托卡尔丘克希望通过她的阅读图谱带领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如何在错觉和流浪中找到真正的自我?
————————
【媒体推荐】
“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
“她运用观照现实的新方法,糅合精深的写实与瞬间的虚幻,观察入微又纵情于神话,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具独创性的散文作家之一。她是位速写大师,捕捉那些在逃避日常生活的人。她写他人所不能写:‘世间那痛彻人心的陌生感。’……她的文风——激荡且富有思想——流溢于其大约十五部的作品中。”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讨论普鲁斯的小说《玩偶》的这部作品,证实了她自身也独具特色。托卡尔丘克可能是她的同代作家中,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了传统——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产生的问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精神社区——的人。书中讨论了科学与艺术,知识与形而上学,个体的内在自由与外在的历史的关系。但书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普鲁斯。托卡尔丘克怀着对老前辈的敬意,缓缓阅读着小说。”
——格拉齐亚·鲍尔库夫斯卡, 波兰文化期刊Res Publica Nova
“《玩偶与珍珠》证明了普鲁斯那部小说的伟大,也记录了托卡尔丘克结合自己的世界观和经历进行的一次私人阅读的体验。她认为《玩偶》是一部启蒙小说,描写了人们寻找,并且找到了生命意义的过程。”
——卡兹米尔茨·麦西格,波兰文艺期刊Fraza
“她以一种来自女性的、天然的细腻与温柔,同时以敏锐的目光,努力沉入万物内心,融为世界的一部分,然后替万物发声,替世界讲述。这是托卡尔丘克的不同之处,也正是她的不凡之处。”
——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教授 赵刚
“托卡尔丘克始终秉承着波兰多元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提出着可以引起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广泛共鸣的普遍问题。”
——波兰驻美国大使 彼得·维尔泽克
“托卡尔丘克跟随着自己的好奇心,大胆地前行,从不受困于种种边界和类型的藩篱。她笔下的人物都鲜活地存在于书页之间,他们发出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巴黎评论》
“在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她是欧洲最重要的人本主义作家之一,致力于欧洲大陆的思想和散文主义小说传统。”
“托卡尔丘克童年时便通过她对童话和神话的敏锐直觉,建构了她对万事万物——人、动物、植物、风景等——之间联系的理解,成为作家后的她试图通过想象力证明,童年时的好奇心并没有被成人社会粗暴地切断,依然在她的作品中延续。”
——《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