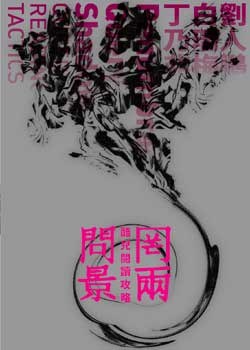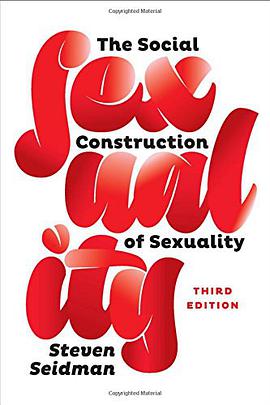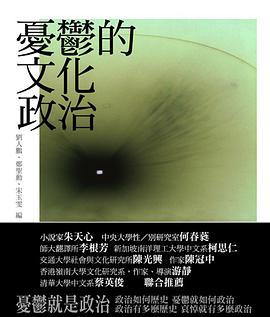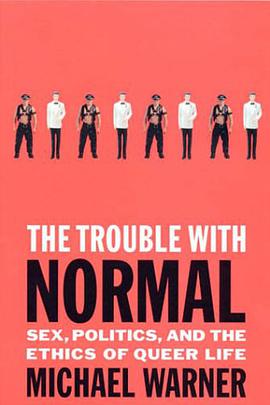罔两问景:酷儿阅读攻略 豆瓣
9.0 (5 个评分)
作者:
刘人鹏
/
白瑞梅
…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2007
景兩問罔︰酷兒閱讀攻略
Penumbrae Query Shadow: Queer Reading Tactics
序:「罔兩問景」方法論
劉人鵬、白瑞梅(Amie Parry)、丁乃非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我們近十年來合作的成果。上個世紀九○年代的台灣,我們在表面蓬勃同時暗潮汹湧的性/別論述與運動中參與、感受、探索、思考。1998年,我們一起到芬蘭參加第二屆Crossroads文化研究世界年會,從搭飛機一直到芬蘭的湖邊、船上,我們一路討論著各自的論文,以及週遭的運動氛圍。芬蘭回來的那個夏天,我們把一路興奮激情的討論成果寫成了〈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的初稿。從此「含蓄」的性政治以及含蓄文本策略的詩學,作為一種上個世紀九○年代台灣強有力的文化-美學殘餘,成為我們持續深入探索的議題。我們認為,含蓄的規訓力道,或許可以用《莊子》寓言「罔兩問景」中「罔兩」提問的模式,當作一種方法,不斷進行詰問。
「罔兩問景」來自《莊子》: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莊子‧齊物論》)
眾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莊子.寓言》)
在這個寓言裏,影子的影子罔兩(影外微陰)向影子提問,問怹為什麼沒有獨立的操守。影子的回答質疑了習以為常的形影關係假設(影依待形),但我們卻在《莊子》文意脈絡之外發現了問題:提問的是罔兩,但影子的思考卻是針對其與「所待」的「形」之間的關係。故事終止於影的回答,然而這個回答是否滿足罔兩的問題,不得而知。罔兩的提問有兩個意義:其一,在一個公私領域都忽略的、人們幾乎看不見(平常誰會注意影子外面猶有微陰,影子還有影子呢?)的位置上,向著常識世界理所當然的主從階序關係提出疑問,並且是對著比較有可能反省這個關係的、被視為從屬性的主體發問;其二,透過一個位於二元性主從階序關係邊緣、難以辨識的位置詰問,文本出現了二元關係之外的聲音,這個聲音之被辨識,也許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於一種貼近發問者的閱讀。有趣的是,〈寓言〉篇稱發問者為「眾罔兩」,提醒了我們:平常能被視為「個體」的,並不是所有的主體,在公私領域難以再現的邊緣位置發聲,通常會被視為「群」或「眾」中的一員。而罔兩被閱讀的可能,也許就在於「眾」,不是由於人多構成群眾,而是由於怹面目模糊卻堅持提問。透過罔兩的提問,主流結構關係要一再被檢視,而閱讀眾罔兩,也使得新的位置以及游移含蓄的策略層出不窮。
▼▼▼
收在書裏的第一篇論文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我們的思索以及彼此之間的熱切討論,政治脈絡可以溯及1997年台北市政府驟然宣布廢除公娼,北台灣婦運組織對於是否要參與公娼的抗爭,彼此之間意見紛歧,婦運內部的裂解形勢逐漸升高。但環繞著公娼議題的歧見,點燃的其實是婦運團體早已蓄勢待發的在「性」政治議題上的新舊衝突,特別是對於「女性」的「性」。所謂舊衝突,指的是:早在九○年代初期,對於女性各種各樣以及各種階級的「性」能動性,就一直有著爭議。例如:傳統「淫婦」的問題、何以面對色情我們只能負面地批評、以及當時有女性主義者理直氣壯地要求「女同性戀你們應該自己站出來為自己說話」,還有爭議娼妓∕性工作者怎麼可以是「女性主義者」等等。結果之一就是1997年《婦女新知》全職女同志工作者被解雇。然而這些事件,不論在運動團體內部或對外,談論的方式總是很含蓄。一方面,強烈感到要忠於過去所共享邊緣化的女性主義價值,而另一方面則面臨一種新興的體制性壓迫(據說婦運組織成長快速,因此操作方式需要「正式化」,某些議題具有優先性,要讓工作更有效率等等),含蓄從上到下作用著,匯集力道,驅逐它要驅逐的對象。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類似的含蓄策略似乎也在學院間運作,特別是對於關乎性/別的議題,經常來自一種崇高的位置,宣稱自己最是善意,並且使用文質彬彬的「儒家」修辭。
因此,「含蓄政略,酷兒詩學」源自我們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瀰漫著的一種文化的、以及文化養成的力道,其效力在於一種主流的倫理,附帶看不見的暴力。比方說,有學問、高學歷、以最有文化教養的方式看似溫柔敦厚的使用語言─這些都構成一種非常主流有力的論述。我們認為,在這個主流論述裏,一個人若是文質彬彬、拒絕面對矛盾衝突,也就被認為在情緒上有修養。這種含蓄文化,以及含蓄如何在文化文本及日常生活操作,我們認為,可以理解為一種「台灣儒家」文化,源自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某種自我權威化以及中國化的教育與文化治安檢查,接合了常民實踐以及民俗信仰,這種氛圍在政權已經轉移後的二十一世紀初,仍然持續著。
我們的方法,主要是在於歷史化,試圖將「含蓄」作為當代規訓策略之殘餘,從上個世紀八○年代晚期,進入九○年代,以解嚴為標誌的十年,直到政權轉移到民進黨,將其持續性及斷裂性都歷史化。談論含蓄以及書寫含蓄的一個困難在於,正當「中國」這個符號已經成為政治禁忌的時刻,這個分析必須脫離未經反思的「中國性」。我們認為,政治兩極化把「中國」事與人都外在化、妖魔化,這種氛圍已經阻礙了長久以來我們早該開始的批判性自我檢視,看到從國民黨統治時期整體性的文化、教育、政治、社會模塑建構中,我們各自不同的棲息於、交疊於、對抗於多種多樣卻相當具有特定性的「台灣」所建構出的「中國性」裏。對我們來說,「含蓄」就是這種台灣建構出的殘餘文化力道之一。批判性的檢視具有關鍵性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主流及反主流的新舊社會力道以及社會主體。
此外,我們有必要區分出不同的含蓄,在規訓性的含蓄以及反含蓄的能動性與諸多策略之間,區辨出不同。然而如果不先分析出主流含蓄如何壓迫或壓抑,我們就無法定位那些馴服不住的、抵抗性的、不合作的或不結盟的含蓄。如果不能辨識主流壓抑性的力道如何透過並且在特定一種(文化上被高舉、被理想化的)含蓄中作用,把含蓄的主體標誌為高度文化修養、自我節制、並且能寬容,那麼,文本以及日常生活中反含蓄的諸多能動性與策略,就太容易被忽略、否認、邊緣化或遺忘,甚至可能被病理化為自棄。在此我們想到台北公娼1997年到1999年之間持續不放棄要求自主與工作權,種種不含蓄、不要臉的街頭抗爭;或者酷兒書寫;或者文學與文化生產者如夏宇的詩、女同志樂團;或者九○年代台灣一些酷兒科幻小說,那些基進性的不合作、不結盟,可以看成是一種反法西斯或反準法西斯的慾望與傾向,在一種並不全然一致全都偏執的狀態下,強調死皮賴臉地活著,作為一種抵抗的模式。檢視主流含蓄如何操作,使得我們可以駁斥主流對於反含蓄策略的閱讀,把反含蓄當成反動或併發症,同時我們也可以開始探索,在這樣維持生命的策略裏,如何可以是一種另類的行動或感受方式。
就分析規訓的效應以及權力的效應而言,傅柯的分析方式確實啟發了我們,但在我們的論文裡並不提傅柯。這有兩個原因:其一,就一種文化與政治的特例分析而言,含蓄與權力如何彼此鑲嵌,我們的研究並未與傅柯的作品交鋒;其二,本研究在一個較廣大的前瞻視野上,關心的是性弱勢的社會正義,而「傅柯」在台灣被使用的情形,有些已經被轉變成與此視界相違。這種情況比較與傅柯作品本身的意義無關,而是它們如何被用在台灣學院論述中,如何被選擇性而去脈絡化地使用。被當成了「理論」後,傅柯作品中法國六○年代活生生的歷史脈絡一方面是消失了,另一方面又同時被定格成不具歷史性的過時「社會解放與性解放」。在某種解釋下,傅柯對於「壓抑」的歷史性理解,變成與全球新自由主義共謀,用來壓抑東亞華人資本主義地區正在成形中的社會運動與新興性革命。我們處在一個「打造國族」很容易把其他議題都擺在一邊的情況下,性的革命以及性的公民權已經成為最關鍵最迫切日常生活公民權對抗國家機器的戰地之一。後法西斯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習慣性地把能動性當成是偏差,在此,猶太基督教文化傳統對窮人與弱者的正當性照顧很少見,只有那些(帶著體制認可標記的)受害者可以享受寬容。在這個脈絡裡,冷戰從未結束,而左翼批判早已經從被禁轉入地下,進一步變成了不愛國(不本土)的污名。這樣的脈絡下,性解放論述與社會革命論述實質上構成了一種「去殖民」的介入。
在後法西斯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含蓄」策略性地在關鍵性的議題上(例如恐同)抑制語言,以便阻止∕保護這種態度不成為公共議題,使它在必要的時候必然成為問題。在關鍵性的議題上抑制語言(恐同),就擔保了問題持續停留在個人行為與情感關係之間的層次;要求程度相當的禮貌,也就同時強迫性地要雙方都有合宜的言行,並以合宜的言行標準衡量雙方。這樣一種修辭交易,形式上是互惠,實質上則是不平等的沈默。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及社會階序之間的權力關係經常藉以維持不變,甚至強化,而為此付出代價的,則是邊緣人、污名化的性實踐。簡而言之,是位置較低以及較缺乏文化資源的一方付出代價。在某些地方(例如台灣),文化是階級與身份的共同決定要素之一:為了滿足各種規訓的需求,並且讓日常生活的矛盾不致於暴露,含蓄修辭策略的散佈,有能力造成並且也的確造成了致命的功效。
含蓄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性的把沈默與言語結合起來的方式。在台灣社會裡,某些場域會比別的場域更多使用含蓄,例如在學校或者其他比較具有文化修養的地方,通常也是經濟上比較優渥的環境(當然也有例外)。我們以「修辭」為起點,當作思考含蓄的一種方式。思考含蓄並不容易,因為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日常生活中,它是以一種美學-倫理情感來操作,有點神秘奧妙,有點神話性地支配,並且在資本主義、極度壓縮的工業化現代性裡,其實沒有人真正擁有含蓄。那是一種台灣國民黨政府治理時期所想像創造的一種「美」與「善」的中華文化,因此我們第一篇論文在發表後聽到一種批評的聲音是:「含蓄是一種傳統的美德,你們怎麼能這樣把它跟權力相提並論。」我們對含蓄的批判,成形於以下的脈絡,同時也是為著這樣的脈絡而提出:馬克思主義對儒家的偽善貶抑性的批判早期已經被噤(當成「左派」),而後來又被污名(當成是「中國」)。這個脈絡是資本主義主導遷台的中國脈絡,在這個脈絡下「含蓄」已經被重新創造為教養以及文明化的知識,並且與教養以及文明化的知識接合。即使從來沒有人真正含蓄,但某些人可以有效運用含蓄,並且在不同脈絡下,不同的主體可以被含蓄規訓,有時候是用非常暴力的方式,但幾乎完全無法被看見。
我們提出「修辭」一詞當作思考含蓄的一種方式,重點在於我們把對於「含蓄」的認知從內容性移轉到語言性,分析它如何在語言中實地操作,並且也透過語言來操作。我們必須強調它的文本性,唯有如此,它的政治意涵才能顯現,而它的規訓力道也才能被分析與批判。在此,「修辭」一詞並非日常意義,在我們的用法裡想要召喚出的是:「含蓄」絕非自然天成,含蓄同時帶著語言與情緒。事實上,「修辭」作為主導性倫理的傳統價值,其中附帶著看不見的暴力,而我們從「修辭」的視角來了解含蓄,就是企圖對這個文化操作賦予政治性的理解。
▼▼▼
如果說本書第一篇〈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著力於揭露、批判、反省主流抑制性的含蓄力道;那麼,第二篇〈陳雪的反寫實、反含蓄〉在於閱讀出一種看不見的「婆」的罔兩位置,勾勒某種對抗性的反含蓄,而「反寫實」在這裏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一種罔兩性的書寫及閱讀策略。第三篇〈鱷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在書寫當時是作為「罔兩問景」寫作計劃三部曲的第二部,我們試著在台灣女同志-女性主義的歷史與運動脈絡中,閱讀早已經發問的某種「眾罔兩」─我們稱之為準T主體。第四篇〈寫實的奇幻結構與奇幻的寫實效應:重讀T、婆敘事〉算是三部曲的第三部,我們重新回到已經被九○年代據說昂揚的同志運動所遺忘的台灣七○年代多少帶著悲情的通俗濫情女同性戀小說,在這一篇裏,「眾罔兩」不僅是文本再現的七○年代台灣T婆,同時也是通俗濫情這個文類本身。
我們把以上四篇稱為「罔兩篇」,紀念的是它力圖理解紛然多元的「眾罔兩」形態,及其試著剖析主流含蓄力道的努力;後面四篇則是「問景篇」,比起前四篇,也許它更想做的是去閱讀不斷發問中的眾罔兩的能動性及其問題,想要像庖丁解牛,在盤根錯節的骨節之間找到遊刃有餘的空間。
第五篇〈自戀與「幫幫忙」樂團的引導問答:台北『地下』拉子〉,閱讀的正是唱歌的「地下拉子」對著形影不離之世界的詰問;第六篇〈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1994幼獅科幻文學獎酷兒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是酷兒科幻小說裏面在「人」與「非人」之間的「後人」眾罔兩的攻略遊戲,多少也呼應著「罔兩篇」處理的寫實、奇幻的結構及效應問題。第七篇〈「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暴力、洪凌科幻小說與酷兒文化批判〉,我們在眾罔兩的詰問裏逼視含蓄的暴力、暴力的含蓄、以及酷兒「暴力」書寫的再現及閱讀政治。最後一篇〈看∕不見疊影:家務與性工作中的婢妾身形〉,試圖進一步描摩生存於「影」當中看不見的眾罔兩,透過卑賤主體,詰問著其實形影不離的家務與性工作,而台灣九○年代性/別與政治場域中「性工作」問題的盤根錯節,正是我們思考階序與含蓄的起點,並且不可能有終點。
八篇論文,不論是我們合寫或各自完成,總是在一種對話的情境裏,在不同的地方延展著我們以「罔兩問景」為方法所作的種種不同層面、不同位置、不同策略的新探索。此外,我們書的英文副標題與馬嘉蘭的文章"Chen Xue's Queer Tactics"類近,同時也特別標記閱讀的過程與實踐。
最後我們想強調的,也是最珍貴的紀念,是這本論文集的合作過程。每一篇論文記錄的,是我們帶著筆記電腦或筆記本,在咖啡店、三溫暖、一起出國開會的旅途及旅館中,或者透過電子郵件,我們的對話、思索與書寫過程。每一篇作品,也鑲嵌在持續進行的團隊研究計劃裏,當然,也印記著我們週遭親愛朋友們的成果以及從未間斷的對話。對於親愛朋友們的感謝,我們分別紀錄在每一篇論文結尾的謝誌裏。在此要致謝的是這幾年國科會提供的研究計劃補助,深深感謝幾個計劃的助理,給了我們最有智慧的協助,讓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彼此學習:謝佩妏、陳祐禎、鄧雅丹、張佳蓉、鄭聖勳、陳慧文、陳采瑛、葉德宣、涂懿美、金宜蓁、劉純瑀、沈慧婷、徐國文。感謝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此書,何春蕤總是那麼鼓舞著我們,細心的提醒,以及好幾篇論文的校對,讓我們驚訝地感謝她有那麼多的精力照顧那麼多的人與事。最讓我們感動的,還有整個出版過程裏編輯玉立付出的心力,她閱讀了每一個字,和我們討論每一個艱澀的詞句,甚至複驗引文,重新整理書目,感謝她一兩年來催促我們交稿,催著我們做這做那,在她眼睛不好的時候,仍然掛記著叮囑我們修改,催促著出版的時程。感謝暐鵬設計這麼充滿罔兩感受的封面。當然,這書一定還有很多的疏失,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不論如何,在此告一段落,我們還要繼續往前走。而在繼續走之前,我們又想到,還要飲水思源,感謝好幾位對我們有啟發性的學者,感謝錢新祖,是他當年講解「罔兩問景」的「另類主體性」,觸動了我們對「罔兩」的一再思索,此刻在酷兒的脈絡裏感謝他,我們猜想他會笑。感謝D.A. Miller多年來持續的啟發,課堂上與書寫中對於英文語境多重向度的含蓄(reticence)與沈默的精彩閱讀和細緻分析。感謝卡維波,雖然他可能因為在這個行列裏像老人般地被感謝而不自在,但他好幾篇罔兩問景般的論文,的確讓我們受益。感謝Lisa Lowe 和Judith Halberstam,因為他們才得以開始思考變態現代性(perverse modernities)的複數性質,還有開始了解queer和正典同性戀(homonormativity)的不同。
Penumbrae Query Shadow: Queer Reading Tactics
序:「罔兩問景」方法論
劉人鵬、白瑞梅(Amie Parry)、丁乃非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我們近十年來合作的成果。上個世紀九○年代的台灣,我們在表面蓬勃同時暗潮汹湧的性/別論述與運動中參與、感受、探索、思考。1998年,我們一起到芬蘭參加第二屆Crossroads文化研究世界年會,從搭飛機一直到芬蘭的湖邊、船上,我們一路討論著各自的論文,以及週遭的運動氛圍。芬蘭回來的那個夏天,我們把一路興奮激情的討論成果寫成了〈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的初稿。從此「含蓄」的性政治以及含蓄文本策略的詩學,作為一種上個世紀九○年代台灣強有力的文化-美學殘餘,成為我們持續深入探索的議題。我們認為,含蓄的規訓力道,或許可以用《莊子》寓言「罔兩問景」中「罔兩」提問的模式,當作一種方法,不斷進行詰問。
「罔兩問景」來自《莊子》: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莊子‧齊物論》)
眾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莊子.寓言》)
在這個寓言裏,影子的影子罔兩(影外微陰)向影子提問,問怹為什麼沒有獨立的操守。影子的回答質疑了習以為常的形影關係假設(影依待形),但我們卻在《莊子》文意脈絡之外發現了問題:提問的是罔兩,但影子的思考卻是針對其與「所待」的「形」之間的關係。故事終止於影的回答,然而這個回答是否滿足罔兩的問題,不得而知。罔兩的提問有兩個意義:其一,在一個公私領域都忽略的、人們幾乎看不見(平常誰會注意影子外面猶有微陰,影子還有影子呢?)的位置上,向著常識世界理所當然的主從階序關係提出疑問,並且是對著比較有可能反省這個關係的、被視為從屬性的主體發問;其二,透過一個位於二元性主從階序關係邊緣、難以辨識的位置詰問,文本出現了二元關係之外的聲音,這個聲音之被辨識,也許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於一種貼近發問者的閱讀。有趣的是,〈寓言〉篇稱發問者為「眾罔兩」,提醒了我們:平常能被視為「個體」的,並不是所有的主體,在公私領域難以再現的邊緣位置發聲,通常會被視為「群」或「眾」中的一員。而罔兩被閱讀的可能,也許就在於「眾」,不是由於人多構成群眾,而是由於怹面目模糊卻堅持提問。透過罔兩的提問,主流結構關係要一再被檢視,而閱讀眾罔兩,也使得新的位置以及游移含蓄的策略層出不窮。
▼▼▼
收在書裏的第一篇論文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我們的思索以及彼此之間的熱切討論,政治脈絡可以溯及1997年台北市政府驟然宣布廢除公娼,北台灣婦運組織對於是否要參與公娼的抗爭,彼此之間意見紛歧,婦運內部的裂解形勢逐漸升高。但環繞著公娼議題的歧見,點燃的其實是婦運團體早已蓄勢待發的在「性」政治議題上的新舊衝突,特別是對於「女性」的「性」。所謂舊衝突,指的是:早在九○年代初期,對於女性各種各樣以及各種階級的「性」能動性,就一直有著爭議。例如:傳統「淫婦」的問題、何以面對色情我們只能負面地批評、以及當時有女性主義者理直氣壯地要求「女同性戀你們應該自己站出來為自己說話」,還有爭議娼妓∕性工作者怎麼可以是「女性主義者」等等。結果之一就是1997年《婦女新知》全職女同志工作者被解雇。然而這些事件,不論在運動團體內部或對外,談論的方式總是很含蓄。一方面,強烈感到要忠於過去所共享邊緣化的女性主義價值,而另一方面則面臨一種新興的體制性壓迫(據說婦運組織成長快速,因此操作方式需要「正式化」,某些議題具有優先性,要讓工作更有效率等等),含蓄從上到下作用著,匯集力道,驅逐它要驅逐的對象。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類似的含蓄策略似乎也在學院間運作,特別是對於關乎性/別的議題,經常來自一種崇高的位置,宣稱自己最是善意,並且使用文質彬彬的「儒家」修辭。
因此,「含蓄政略,酷兒詩學」源自我們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瀰漫著的一種文化的、以及文化養成的力道,其效力在於一種主流的倫理,附帶看不見的暴力。比方說,有學問、高學歷、以最有文化教養的方式看似溫柔敦厚的使用語言─這些都構成一種非常主流有力的論述。我們認為,在這個主流論述裏,一個人若是文質彬彬、拒絕面對矛盾衝突,也就被認為在情緒上有修養。這種含蓄文化,以及含蓄如何在文化文本及日常生活操作,我們認為,可以理解為一種「台灣儒家」文化,源自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某種自我權威化以及中國化的教育與文化治安檢查,接合了常民實踐以及民俗信仰,這種氛圍在政權已經轉移後的二十一世紀初,仍然持續著。
我們的方法,主要是在於歷史化,試圖將「含蓄」作為當代規訓策略之殘餘,從上個世紀八○年代晚期,進入九○年代,以解嚴為標誌的十年,直到政權轉移到民進黨,將其持續性及斷裂性都歷史化。談論含蓄以及書寫含蓄的一個困難在於,正當「中國」這個符號已經成為政治禁忌的時刻,這個分析必須脫離未經反思的「中國性」。我們認為,政治兩極化把「中國」事與人都外在化、妖魔化,這種氛圍已經阻礙了長久以來我們早該開始的批判性自我檢視,看到從國民黨統治時期整體性的文化、教育、政治、社會模塑建構中,我們各自不同的棲息於、交疊於、對抗於多種多樣卻相當具有特定性的「台灣」所建構出的「中國性」裏。對我們來說,「含蓄」就是這種台灣建構出的殘餘文化力道之一。批判性的檢視具有關鍵性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主流及反主流的新舊社會力道以及社會主體。
此外,我們有必要區分出不同的含蓄,在規訓性的含蓄以及反含蓄的能動性與諸多策略之間,區辨出不同。然而如果不先分析出主流含蓄如何壓迫或壓抑,我們就無法定位那些馴服不住的、抵抗性的、不合作的或不結盟的含蓄。如果不能辨識主流壓抑性的力道如何透過並且在特定一種(文化上被高舉、被理想化的)含蓄中作用,把含蓄的主體標誌為高度文化修養、自我節制、並且能寬容,那麼,文本以及日常生活中反含蓄的諸多能動性與策略,就太容易被忽略、否認、邊緣化或遺忘,甚至可能被病理化為自棄。在此我們想到台北公娼1997年到1999年之間持續不放棄要求自主與工作權,種種不含蓄、不要臉的街頭抗爭;或者酷兒書寫;或者文學與文化生產者如夏宇的詩、女同志樂團;或者九○年代台灣一些酷兒科幻小說,那些基進性的不合作、不結盟,可以看成是一種反法西斯或反準法西斯的慾望與傾向,在一種並不全然一致全都偏執的狀態下,強調死皮賴臉地活著,作為一種抵抗的模式。檢視主流含蓄如何操作,使得我們可以駁斥主流對於反含蓄策略的閱讀,把反含蓄當成反動或併發症,同時我們也可以開始探索,在這樣維持生命的策略裏,如何可以是一種另類的行動或感受方式。
就分析規訓的效應以及權力的效應而言,傅柯的分析方式確實啟發了我們,但在我們的論文裡並不提傅柯。這有兩個原因:其一,就一種文化與政治的特例分析而言,含蓄與權力如何彼此鑲嵌,我們的研究並未與傅柯的作品交鋒;其二,本研究在一個較廣大的前瞻視野上,關心的是性弱勢的社會正義,而「傅柯」在台灣被使用的情形,有些已經被轉變成與此視界相違。這種情況比較與傅柯作品本身的意義無關,而是它們如何被用在台灣學院論述中,如何被選擇性而去脈絡化地使用。被當成了「理論」後,傅柯作品中法國六○年代活生生的歷史脈絡一方面是消失了,另一方面又同時被定格成不具歷史性的過時「社會解放與性解放」。在某種解釋下,傅柯對於「壓抑」的歷史性理解,變成與全球新自由主義共謀,用來壓抑東亞華人資本主義地區正在成形中的社會運動與新興性革命。我們處在一個「打造國族」很容易把其他議題都擺在一邊的情況下,性的革命以及性的公民權已經成為最關鍵最迫切日常生活公民權對抗國家機器的戰地之一。後法西斯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習慣性地把能動性當成是偏差,在此,猶太基督教文化傳統對窮人與弱者的正當性照顧很少見,只有那些(帶著體制認可標記的)受害者可以享受寬容。在這個脈絡裡,冷戰從未結束,而左翼批判早已經從被禁轉入地下,進一步變成了不愛國(不本土)的污名。這樣的脈絡下,性解放論述與社會革命論述實質上構成了一種「去殖民」的介入。
在後法西斯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含蓄」策略性地在關鍵性的議題上(例如恐同)抑制語言,以便阻止∕保護這種態度不成為公共議題,使它在必要的時候必然成為問題。在關鍵性的議題上抑制語言(恐同),就擔保了問題持續停留在個人行為與情感關係之間的層次;要求程度相當的禮貌,也就同時強迫性地要雙方都有合宜的言行,並以合宜的言行標準衡量雙方。這樣一種修辭交易,形式上是互惠,實質上則是不平等的沈默。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及社會階序之間的權力關係經常藉以維持不變,甚至強化,而為此付出代價的,則是邊緣人、污名化的性實踐。簡而言之,是位置較低以及較缺乏文化資源的一方付出代價。在某些地方(例如台灣),文化是階級與身份的共同決定要素之一:為了滿足各種規訓的需求,並且讓日常生活的矛盾不致於暴露,含蓄修辭策略的散佈,有能力造成並且也的確造成了致命的功效。
含蓄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性的把沈默與言語結合起來的方式。在台灣社會裡,某些場域會比別的場域更多使用含蓄,例如在學校或者其他比較具有文化修養的地方,通常也是經濟上比較優渥的環境(當然也有例外)。我們以「修辭」為起點,當作思考含蓄的一種方式。思考含蓄並不容易,因為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日常生活中,它是以一種美學-倫理情感來操作,有點神秘奧妙,有點神話性地支配,並且在資本主義、極度壓縮的工業化現代性裡,其實沒有人真正擁有含蓄。那是一種台灣國民黨政府治理時期所想像創造的一種「美」與「善」的中華文化,因此我們第一篇論文在發表後聽到一種批評的聲音是:「含蓄是一種傳統的美德,你們怎麼能這樣把它跟權力相提並論。」我們對含蓄的批判,成形於以下的脈絡,同時也是為著這樣的脈絡而提出:馬克思主義對儒家的偽善貶抑性的批判早期已經被噤(當成「左派」),而後來又被污名(當成是「中國」)。這個脈絡是資本主義主導遷台的中國脈絡,在這個脈絡下「含蓄」已經被重新創造為教養以及文明化的知識,並且與教養以及文明化的知識接合。即使從來沒有人真正含蓄,但某些人可以有效運用含蓄,並且在不同脈絡下,不同的主體可以被含蓄規訓,有時候是用非常暴力的方式,但幾乎完全無法被看見。
我們提出「修辭」一詞當作思考含蓄的一種方式,重點在於我們把對於「含蓄」的認知從內容性移轉到語言性,分析它如何在語言中實地操作,並且也透過語言來操作。我們必須強調它的文本性,唯有如此,它的政治意涵才能顯現,而它的規訓力道也才能被分析與批判。在此,「修辭」一詞並非日常意義,在我們的用法裡想要召喚出的是:「含蓄」絕非自然天成,含蓄同時帶著語言與情緒。事實上,「修辭」作為主導性倫理的傳統價值,其中附帶著看不見的暴力,而我們從「修辭」的視角來了解含蓄,就是企圖對這個文化操作賦予政治性的理解。
▼▼▼
如果說本書第一篇〈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著力於揭露、批判、反省主流抑制性的含蓄力道;那麼,第二篇〈陳雪的反寫實、反含蓄〉在於閱讀出一種看不見的「婆」的罔兩位置,勾勒某種對抗性的反含蓄,而「反寫實」在這裏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一種罔兩性的書寫及閱讀策略。第三篇〈鱷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在書寫當時是作為「罔兩問景」寫作計劃三部曲的第二部,我們試著在台灣女同志-女性主義的歷史與運動脈絡中,閱讀早已經發問的某種「眾罔兩」─我們稱之為準T主體。第四篇〈寫實的奇幻結構與奇幻的寫實效應:重讀T、婆敘事〉算是三部曲的第三部,我們重新回到已經被九○年代據說昂揚的同志運動所遺忘的台灣七○年代多少帶著悲情的通俗濫情女同性戀小說,在這一篇裏,「眾罔兩」不僅是文本再現的七○年代台灣T婆,同時也是通俗濫情這個文類本身。
我們把以上四篇稱為「罔兩篇」,紀念的是它力圖理解紛然多元的「眾罔兩」形態,及其試著剖析主流含蓄力道的努力;後面四篇則是「問景篇」,比起前四篇,也許它更想做的是去閱讀不斷發問中的眾罔兩的能動性及其問題,想要像庖丁解牛,在盤根錯節的骨節之間找到遊刃有餘的空間。
第五篇〈自戀與「幫幫忙」樂團的引導問答:台北『地下』拉子〉,閱讀的正是唱歌的「地下拉子」對著形影不離之世界的詰問;第六篇〈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1994幼獅科幻文學獎酷兒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是酷兒科幻小說裏面在「人」與「非人」之間的「後人」眾罔兩的攻略遊戲,多少也呼應著「罔兩篇」處理的寫實、奇幻的結構及效應問題。第七篇〈「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暴力、洪凌科幻小說與酷兒文化批判〉,我們在眾罔兩的詰問裏逼視含蓄的暴力、暴力的含蓄、以及酷兒「暴力」書寫的再現及閱讀政治。最後一篇〈看∕不見疊影:家務與性工作中的婢妾身形〉,試圖進一步描摩生存於「影」當中看不見的眾罔兩,透過卑賤主體,詰問著其實形影不離的家務與性工作,而台灣九○年代性/別與政治場域中「性工作」問題的盤根錯節,正是我們思考階序與含蓄的起點,並且不可能有終點。
八篇論文,不論是我們合寫或各自完成,總是在一種對話的情境裏,在不同的地方延展著我們以「罔兩問景」為方法所作的種種不同層面、不同位置、不同策略的新探索。此外,我們書的英文副標題與馬嘉蘭的文章"Chen Xue's Queer Tactics"類近,同時也特別標記閱讀的過程與實踐。
最後我們想強調的,也是最珍貴的紀念,是這本論文集的合作過程。每一篇論文記錄的,是我們帶著筆記電腦或筆記本,在咖啡店、三溫暖、一起出國開會的旅途及旅館中,或者透過電子郵件,我們的對話、思索與書寫過程。每一篇作品,也鑲嵌在持續進行的團隊研究計劃裏,當然,也印記著我們週遭親愛朋友們的成果以及從未間斷的對話。對於親愛朋友們的感謝,我們分別紀錄在每一篇論文結尾的謝誌裏。在此要致謝的是這幾年國科會提供的研究計劃補助,深深感謝幾個計劃的助理,給了我們最有智慧的協助,讓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彼此學習:謝佩妏、陳祐禎、鄧雅丹、張佳蓉、鄭聖勳、陳慧文、陳采瑛、葉德宣、涂懿美、金宜蓁、劉純瑀、沈慧婷、徐國文。感謝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此書,何春蕤總是那麼鼓舞著我們,細心的提醒,以及好幾篇論文的校對,讓我們驚訝地感謝她有那麼多的精力照顧那麼多的人與事。最讓我們感動的,還有整個出版過程裏編輯玉立付出的心力,她閱讀了每一個字,和我們討論每一個艱澀的詞句,甚至複驗引文,重新整理書目,感謝她一兩年來催促我們交稿,催著我們做這做那,在她眼睛不好的時候,仍然掛記著叮囑我們修改,催促著出版的時程。感謝暐鵬設計這麼充滿罔兩感受的封面。當然,這書一定還有很多的疏失,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不論如何,在此告一段落,我們還要繼續往前走。而在繼續走之前,我們又想到,還要飲水思源,感謝好幾位對我們有啟發性的學者,感謝錢新祖,是他當年講解「罔兩問景」的「另類主體性」,觸動了我們對「罔兩」的一再思索,此刻在酷兒的脈絡裏感謝他,我們猜想他會笑。感謝D.A. Miller多年來持續的啟發,課堂上與書寫中對於英文語境多重向度的含蓄(reticence)與沈默的精彩閱讀和細緻分析。感謝卡維波,雖然他可能因為在這個行列裏像老人般地被感謝而不自在,但他好幾篇罔兩問景般的論文,的確讓我們受益。感謝Lisa Lowe 和Judith Halberstam,因為他們才得以開始思考變態現代性(perverse modernities)的複數性質,還有開始了解queer和正典同性戀(homonormativity)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