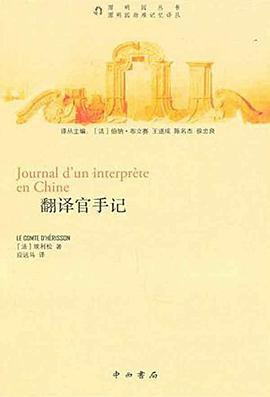翻译官手记 豆瓣
作者:
埃利松
中西书局
2011
- 1
埃利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是最值得一读的关于1860年征战的一本著作,因为它或许是一本写得最为生动最为精彩的著作。 莫里斯·伊里松(Maurice Irisson)在1886年才出版了这本书,署名是埃利松伯爵。年仅20岁,他就陪同蒙托邦将军去了中国,当时的身份是翻译,不是中文翻译,而是英语翻译。因此,他负责与英国盟军的沟通与联络。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等待了25年,目的是不想过于冒犯敏感的英国人,他在书中谴责了英国人想在军事和外交上独占鳌头的野心。总之,在这场对华征战期间,他们以远征军的领导者自居,在法国盟军面前盛气凌人,极力贬低法国人的形象。这也是一本完全是为蒙托邦将军的荣耀而写的书。 作者所展示的史实也是有待商榷的。他经常会拿史实自由发挥。尽管如此,埃利松伯爵的这本著作是一部笔调生动、引人人胜的文献。可以带着轻松快乐的心情阅读本书。 一定要读一下他初到上海时的那段叙述,以及他对这座中国城市的描写。他的《翻译官手记》中最出名的几个章节是关于圆明园大洗劫的,这几个章节更值得一读。夏宫受到中国数代皇帝的青睐,他重墨描写了被毁之前的夏宫,在专栏作者之中,做这种描写的作者为数极少。埃利松伯爵笔下的圆明园洗劫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他的叙述诙谐风趣,洗劫的悲惨景象跃然纸上。其实,他嘲讽了法国人在洗劫圆明园时的混乱无序。 当然,他把洗劫的规模和法英联军的破坏缩小了,他没有谴责这些掠夺行为。但是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由一个专栏作者写的这部文献还是很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