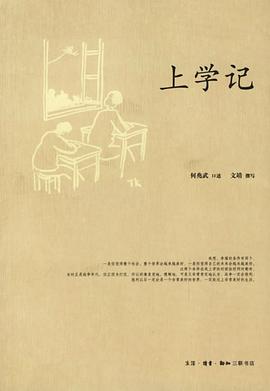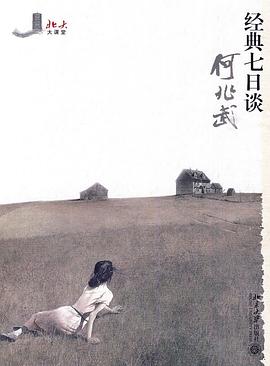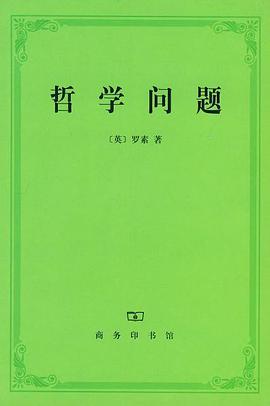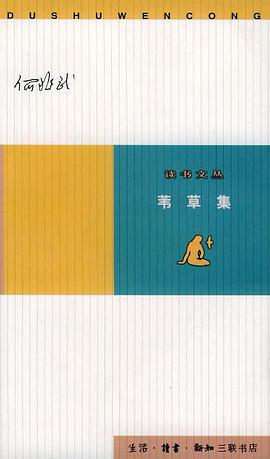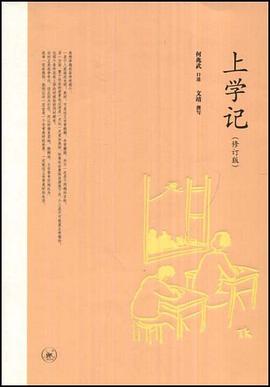何兆武
上学记 豆瓣 Goodreads
9.1 (100 个评分)
作者:
何兆武
/
文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8
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
哲学问题 豆瓣
10.0 (5 个评分)
作者:
罗素
译者:
何兆武
商务印书馆
1999
- 1
本书作者、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当代西方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在数理逻辑的研究领域曾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由于他多方面的成就,他一生曾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1950年的诺贝尔奖。在哲学上,他的观点大抵早期是属于新实在主义的,晚年逐渐转向逻辑实证主义。本书是他早期的最后著作之一,书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许多哲学问题的论点,可以代表他早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在本书各章中,我主要限于谈论那些我认为可以发表一点肯定的和建设性意见的问题,因为单纯否定的批判似乎是不适当的。为了这个缘故,本书中知识论所占篇幅就比形而上学更多些,而哲学家们讨论得很多的一些论题,倘使加以处理,也处理得非常简略。
在本书各章中,我主要限于谈论那些我认为可以发表一点肯定的和建设性意见的问题,因为单纯否定的批判似乎是不适当的。为了这个缘故,本书中知识论所占篇幅就比形而上学更多些,而哲学家们讨论得很多的一些论题,倘使加以处理,也处理得非常简略。
文化漫谈 豆瓣
作者:
何兆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本书大部分篇幅是何兆武先生在清华大学针对本科生有关文化问题的谈话与讲演;主要是探讨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全书共分九讲,每讲集中探讨一个问题,从对西方文化史的介绍切入,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讲解,涉及的知识面甚广;所举实例甚多。此外,何先生对“中学”与“西学”之争、五四运动、胡适、新儒学等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作者将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以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读来有如亲耳聆听先生的讲话。
上学记 豆瓣 Goodreads
9.0 (47 个评分)
作者:
何兆武(口述)
/
文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9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豆瓣
作者:
何兆武
商务印书馆
1999
- 1
编者序言
三年前商务印书馆委托我编纂一部近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涵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经过和几位同志磋商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承担下来。
不用说,这方面的资料浩如烟海,要想编纂一部比较全面的选集,诚非易事。我们从此前斯特恩(Fritz Stern)、盖德纳(Patrick Gardiner)、梅叶霍夫(Hans Meyerhoff)和张文杰兄的各家选本(而尤其是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巨著《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线索;但最后的选择和取舍,终究是要由自己做出,而不能、也不应简单地抄袭前人。古往今来的一切选家,总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理解来进行选择;因此没有两种选本是雷同的,我们目前的这个选本也不例外。虽然为了搜集、挑选和翻译这些资料,我们也曾付出不少劳动,但遗憾的是有些材料仍一时未能找到,有些选择限于我们的水平未必妥当,而我们译文中的错误和抵悟也不敢自保。这项工作已进行三年有余,不宜再拖,所以暂先结集出版。如有可能,希望过些年后出下一版时,根据专家和读者们的意见以及我们自己今后可能有所提高的水平,再加以增删和核定。
书中所选材料,凡是有中文译本的,我们都尽量采用中文译本;至于没有中文译本的,均由我们自己动手译出。可能我们的译文在数量上要比已有的译文,还更多一些。由于译文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手,所以从文字到内容都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已无法强行统一。这一缺点,尚乞读者垂鉴。原文的出处、选者、译者,都已在各章的末尾注明。
参加本书编选和翻译工作的,是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以下工作人员(按姓名笔划):刘鑫、李春平、何冰、何兆武、张立平、柳卸林、程钢、程捷、蒋劲松。最初的提纲是由我草拟的,后来在工作过程中又经过各个参加工作同志的商讨和修订,最后遂呈现为本书目前的面貌。主编工作原请柳卸林同志担任,其后他因工作调动不能继续担任,遂仍由我承乏。程钢同志对全书的组织和统一,做了许多工作。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羊涤生、钱逊、胡伟希、张金华。韩晓华、阎秀芝、张淑琴等同志,商务印书馆的陈应年、武维琴、陈兆福等同志,都曾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何兆武谨记
92年9月 北京清华园
三年前商务印书馆委托我编纂一部近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涵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经过和几位同志磋商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承担下来。
不用说,这方面的资料浩如烟海,要想编纂一部比较全面的选集,诚非易事。我们从此前斯特恩(Fritz Stern)、盖德纳(Patrick Gardiner)、梅叶霍夫(Hans Meyerhoff)和张文杰兄的各家选本(而尤其是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巨著《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线索;但最后的选择和取舍,终究是要由自己做出,而不能、也不应简单地抄袭前人。古往今来的一切选家,总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理解来进行选择;因此没有两种选本是雷同的,我们目前的这个选本也不例外。虽然为了搜集、挑选和翻译这些资料,我们也曾付出不少劳动,但遗憾的是有些材料仍一时未能找到,有些选择限于我们的水平未必妥当,而我们译文中的错误和抵悟也不敢自保。这项工作已进行三年有余,不宜再拖,所以暂先结集出版。如有可能,希望过些年后出下一版时,根据专家和读者们的意见以及我们自己今后可能有所提高的水平,再加以增删和核定。
书中所选材料,凡是有中文译本的,我们都尽量采用中文译本;至于没有中文译本的,均由我们自己动手译出。可能我们的译文在数量上要比已有的译文,还更多一些。由于译文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手,所以从文字到内容都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已无法强行统一。这一缺点,尚乞读者垂鉴。原文的出处、选者、译者,都已在各章的末尾注明。
参加本书编选和翻译工作的,是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以下工作人员(按姓名笔划):刘鑫、李春平、何冰、何兆武、张立平、柳卸林、程钢、程捷、蒋劲松。最初的提纲是由我草拟的,后来在工作过程中又经过各个参加工作同志的商讨和修订,最后遂呈现为本书目前的面貌。主编工作原请柳卸林同志担任,其后他因工作调动不能继续担任,遂仍由我承乏。程钢同志对全书的组织和统一,做了许多工作。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羊涤生、钱逊、胡伟希、张金华。韩晓华、阎秀芝、张淑琴等同志,商务印书馆的陈应年、武维琴、陈兆福等同志,都曾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何兆武谨记
92年9月 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