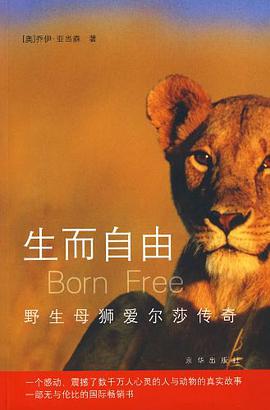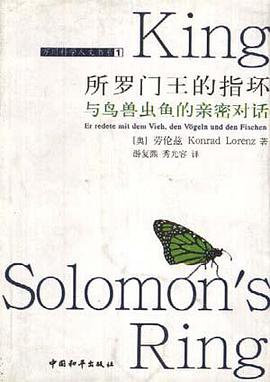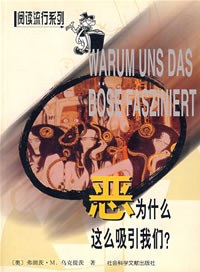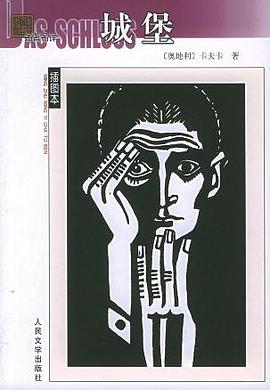生而自由 豆瓣
作者:
[奥地利] 乔伊·亚当森
译者:
张雪兰
京华出版社
2008
- 1
《生而自由:野生母狮爱尔莎传奇》是一头野生狮子:爱尔莎与作者之间生动而感人的真实故事。在非洲的原始荒原上,由于一次意外的误杀,三头失去了母亲的小狮子闯入了作者乔伊?亚当森的生命。就在这片荒原上,乔伊精心抚养着它们,并根据她们不同的个性为她们起了名字,其中最小的那只便是爱尔莎。等小狮子们稍大一些的时候,乔伊把那两只大的送到了荷兰动物园,留下了最小的爱尔莎,因为狮群中最弱小的那只往往活不下来。自此,爱尔莎成了乔伊生活中的一部分,她们同吃、同住、同玩儿,同在非洲荒原的荆棘丛和高山的大森林中漫步徜徉,同在大海的浪花中嬉戏,形同母女又似朋友,由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爱尔莎极其喜欢同丛林里的其他野生动物玩耍,她搞恶作剧一般地追逐着斑马群,她喜欢在厚皮食草动物的粪便中打滚,她也曾失魂落魄地在丛林中寻找另一头公狮的吼声……转眼间,爱尔莎到了自立的年龄,乔伊决定让她重返大自然去过独立自由的生活,于是对爱尔莎进行了野化训练,通过多次努力,爱尔莎终于一步三回头地向荒原深处走去……心有不舍的乔伊望着远去的爱尔莎,泪眼模糊,但对于爱尔莎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因为她天生就是自由的。
书中难得一见的照片令人震撼,有可爱的狮子、大象、其他动物以及东部非洲原生态的风光,在这里,人与动物那自然淳朴的感情超越了一切,全然没有了人兽之分。
书中难得一见的照片令人震撼,有可爱的狮子、大象、其他动物以及东部非洲原生态的风光,在这里,人与动物那自然淳朴的感情超越了一切,全然没有了人兽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