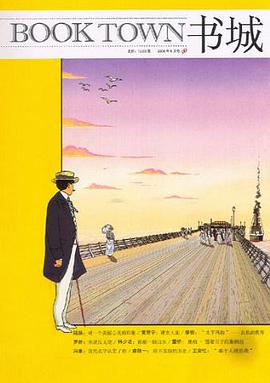读书 豆瓣
8.1 (32 个评分)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读书》创刊号
《读书》创刊伊始,就发出了反映读书界共同心声的呐喊:“读书无禁区。”其继承了中国知识界的淑世情怀和传统,以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以其思想的开放,议论的清新,文风的隽永,赢得了读书界的青睐。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众口,体现了读书界对于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 《读书》杂志自从一创刊,就定位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这样的定位,既有别于专业学术研究刊物,也有别于一般大众通俗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读书界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所谓读书界,意指高度关注思想文化领域以及相应书籍出版的一个读者群。尽管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经历了种种社会分化,但这样一个读者群体今天依然存在。《读书》过去常年举行的一项活动就叫做“读书服务日”,既体现了杂志的编辑宗旨,也体现了三联书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读书》杂志是一个为知识界服务的刊物,同时也是一个读书界共用的交流思想、知识和文化的平台。她尽力体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所思所感,展现他们的知性与感性生活,努力提供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应当说,《读书》杂志的这一定位,使其在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刊物之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读书》杂志不是专门的学术刊物,因此,那些只有少数专业研究者才感兴趣的学术专门课题,不是编者关注的中心。《读书》杂志长期致力于从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文化内容,将它们呈现给读者。《读书》杂志既非学术也非通俗的定位,决定了她所刊发的文章与学术论文的文体风格迥然有别,她倡导承继中西文化中优美、形象、鲜明、生动的文章传统,希望尽量少用艰深晦涩的专门术语和“行业黑话”写作,以便让隔行的读书人都能够读懂。 从创刊迄今,《读书》杂志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周年。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见证者,《读书》记录了这个时代各种思潮的起伏跌宕,兴衰际遇,也映现出思想文化界忧戚喜乐的感情律动;既形成了一定的品牌优势,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自由思想,人文关怀。《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读书》创刊伊始,就发出了反映读书界共同心声的呐喊:“读书无禁区。”其继承了中国知识界的淑世情怀和传统,以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以其思想的开放,议论的清新,文风的隽永,赢得了读书界的青睐。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众口,体现了读书界对于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 《读书》杂志自从一创刊,就定位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这样的定位,既有别于专业学术研究刊物,也有别于一般大众通俗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读书界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所谓读书界,意指高度关注思想文化领域以及相应书籍出版的一个读者群。尽管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经历了种种社会分化,但这样一个读者群体今天依然存在。《读书》过去常年举行的一项活动就叫做“读书服务日”,既体现了杂志的编辑宗旨,也体现了三联书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读书》杂志是一个为知识界服务的刊物,同时也是一个读书界共用的交流思想、知识和文化的平台。她尽力体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所思所感,展现他们的知性与感性生活,努力提供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应当说,《读书》杂志的这一定位,使其在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刊物之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读书》杂志不是专门的学术刊物,因此,那些只有少数专业研究者才感兴趣的学术专门课题,不是编者关注的中心。《读书》杂志长期致力于从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文化内容,将它们呈现给读者。《读书》杂志既非学术也非通俗的定位,决定了她所刊发的文章与学术论文的文体风格迥然有别,她倡导承继中西文化中优美、形象、鲜明、生动的文章传统,希望尽量少用艰深晦涩的专门术语和“行业黑话”写作,以便让隔行的读书人都能够读懂。 从创刊迄今,《读书》杂志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周年。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见证者,《读书》记录了这个时代各种思潮的起伏跌宕,兴衰际遇,也映现出思想文化界忧戚喜乐的感情律动;既形成了一定的品牌优势,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自由思想,人文关怀。《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