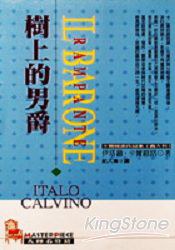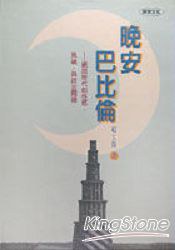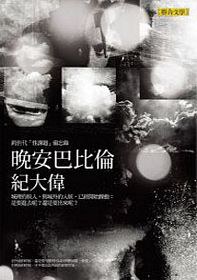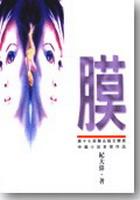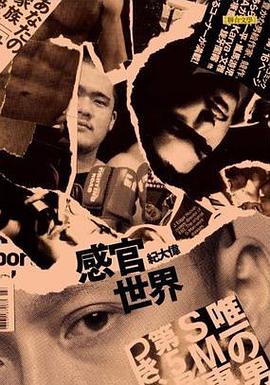在座談會或媒體錄音錄影之類的場合, 節目主持人經常以「酷兒作家」之類的稱呼套在我頭上——妙的是, 這位主持人往往會接著問我:「『酷兒』是什麼?」
這每每讓我納罕: 如果「酷兒」的定義不為人知, 怎會用這個詞來定義我呢?
「酷兒」和許多新鮮辭彙一樣, 雖然人們說不出它的意義, 卻照樣存活甚至流行——公車車廂出現「酷兒內褲」廣告, 電腦網路裡推銷的色情光碟叫「酷兒光碟」。溯想一九九四年, 洪凌、但唐謨和我參與編輯《島嶼邊緣》季刊的「酷兒專輯」時, 應沒想到酷兒的生命竟如此流變。
※「酷兒」不等於「QUEER」※
當時「酷兒專輯」執意啟用新詞, 以便描述某些和「同志」形似、卻仍有所差異的炫惑和慾望。正好, 九O年代起陸續引進台灣的「NewQueer Cinema」展現了上述難以明確描述的差異性: 在賈曼的《愛德華二世》, 湯姆.凱林的《意亂情迷》(Swoon)等等影片中, 可以看見「某種」同性情慾的狂野不羈, 大大不同於平時看見的同志形象。於是我們借取了英文「queer」, 並找了一個俏皮譯名,「酷兒」。
後來每當別人問起「酷兒」的身世時, 我就提出當時翻譯的想法。可是我發現, 這種說法在試圖定義酷兒的過程中, 也有破綻。有兩種質問和我發現的破綻有關; 我要加以回應——在回應過程中, 酷兒的妖性可能更容易揣摹。
第一種質問是: 中文的「酷兒」是「queer」的忠實翻譯嗎?
有人覺得酷兒並不貼切:「queer」在國外本來是用來罵同性戀的粗話,後來被同性戀人士挪用, 可是「queer」的詛咒色彩並沒有在「酷兒」上頭充份還魂。此外,「酷兒」在台灣引發的酷炫想像, 也很難譯回原來的「queer」。
我的回答是: 的確, 酷兒並非全然等於「queer」——雖說前者是後者的翻譯。不過我也要指出, 恐怕也沒有其他中文詞語可以「全然忠實」譯出「queer」——因為「queer」一詞出自於英美情慾歷史, 既然台灣沒有同樣的文化脈絡, 也就養不出「queer」這個字; 如果真要翻譯, 譯出來的結果一定和原版不同、必然沾染本地色彩。「酷兒」是文化交匯下的「雜種」。
這個雜種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原版」的「queer」表示出亦步亦趨的忠實。酷兒就是混血之後的新品種, 要同時面對外來刺激,以及在地歷史。雖然酷兒在台灣的流傳路徑有點傳奇, 但也無可厚非: 畢竟只有活的字詞才為人所用; 堅持潔癖的語彙反而要面對衰亡。
※什麼是「酷兒」?※
第二種質問, 聽起來更尋常, 卻更是棘手:「酷兒」是什麼?——延伸出來的問題是,「酷兒文學」展現什麼特色?
人們面對新詞時, 往往急於詮釋, 並賦予清楚定位。於是我聽聞竟有人說, 酷兒文學就是以同性戀內容為主的性變態科幻小說(或恐怖小說)。不過我卻認為, 酷兒(及文學)未必要動用奇幻場景, 也沒必要呈現奇觀(如性虐待)。特技表演不是酷兒和酷兒文學的必備要素。
但是——如果連以上這些容易辨識的特徵都未必能名定義酷兒, 又該如何指認酷兒?
在此我想提出一種弔詭的「定義」: 酷兒是拒絕被定義的, 它沒有固定的身份認同。
但為了權宜之計, 我仍要為酷兒捕風捉影。就從「身份認同」(identity)下手吧: 同志主張身份認同, 但是酷兒卻加以質疑。
認同強調了同志之間的類同: 在認同的大傘之下, 每個同志都有相似的經驗和歷史。但在強調同質性的時候, 很容易就忽視了群體之內的差異性。在都有同志認同的一群人當中, 並非每個人都過著理所當然的同志生活: 有人雙性戀, 有人愛家人, 有人易裝, 有人變性。
酷兒電影/文學之所以經常出現情色暴力, 是為了說出「同志認同」以及「異性戀認同」無暇顧及的部份: 重點在於標準之外的異質聲音, 變態大觀反而可有可無。以上述電影《意亂情迷》為例: 片中男同性戀情侶濫殺無辜——其「酷兒/queer」之處, 並不在於暴力, 而在於跳脫乖巧守份的美國男同志認同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