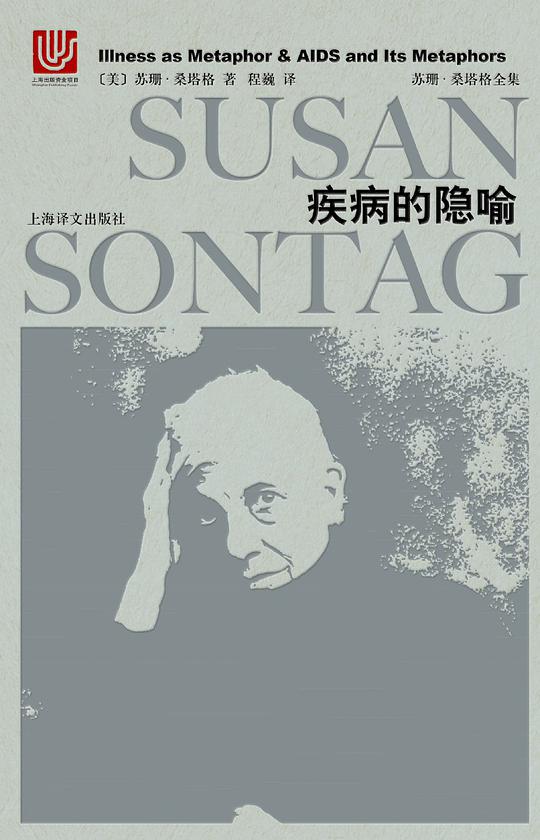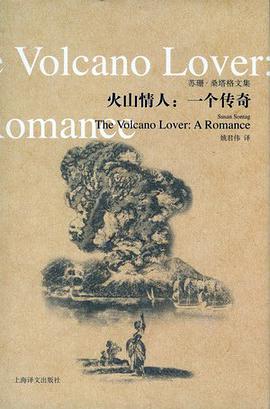疾病的隐喻(2018年版) (苏珊·桑塔格全集) [图书] 豆瓣 Goodreads
Illness as Metaphor & AIDS and Its Metaphors
8.3 (40 个评分)
作者:
(美)苏珊·桑塔格
译者:
程巍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4
其它标题:
疾病的隐喻(全布面精装)
♦ “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所有作品首次以全集面貌展现,全布面典雅精装。
♦ 剥除掉疾病千百年来在文化中被误解的种种迷思,呈现出它们的真正意义。
♦ 本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对医学专业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患者与照护者,造成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苏珊•桑塔格(Susan Santag,1933—2004)
美国作家、评论家、女权主义者,当代西方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一位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的公众良心”、“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3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及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 “苏珊•桑塔格全集”是她所有作品的汇编,分为 “论著”和 “文学”两大板块(并包括其子戴维•里夫编辑的“日记”两卷),共16卷,280余万字。“苏珊•桑塔格全集”是迄今为止整个华语世界引进出版的最大规模的当代西方主流思想家、评论家以及文学家的作品全集,而且是独家版权,在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界、评论界、文学和文化界以及出版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苏珊·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 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 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 结成册出版,《疾病的隐喻》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 ★ 桑塔格总是能让笔下事物焕发新意,即使是不同意她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文字的魅力。
——《新共和》杂志文学编辑莱昂·威瑟提尔
★ 桑塔格的去世,让人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更少了一个如此清楚冷静并具有良知的人。
——诗人、翻译家黄灿然
♦ 剥除掉疾病千百年来在文化中被误解的种种迷思,呈现出它们的真正意义。
♦ 本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对医学专业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患者与照护者,造成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苏珊•桑塔格(Susan Santag,1933—2004)
美国作家、评论家、女权主义者,当代西方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一位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的公众良心”、“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3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及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 “苏珊•桑塔格全集”是她所有作品的汇编,分为 “论著”和 “文学”两大板块(并包括其子戴维•里夫编辑的“日记”两卷),共16卷,280余万字。“苏珊•桑塔格全集”是迄今为止整个华语世界引进出版的最大规模的当代西方主流思想家、评论家以及文学家的作品全集,而且是独家版权,在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界、评论界、文学和文化界以及出版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苏珊·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 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 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 结成册出版,《疾病的隐喻》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 ★ 桑塔格总是能让笔下事物焕发新意,即使是不同意她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文字的魅力。
——《新共和》杂志文学编辑莱昂·威瑟提尔
★ 桑塔格的去世,让人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更少了一个如此清楚冷静并具有良知的人。
——诗人、翻译家黄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