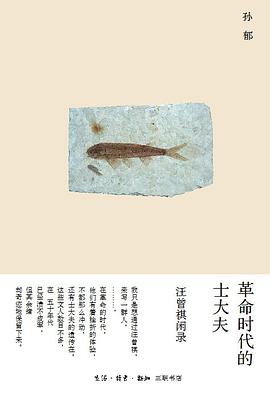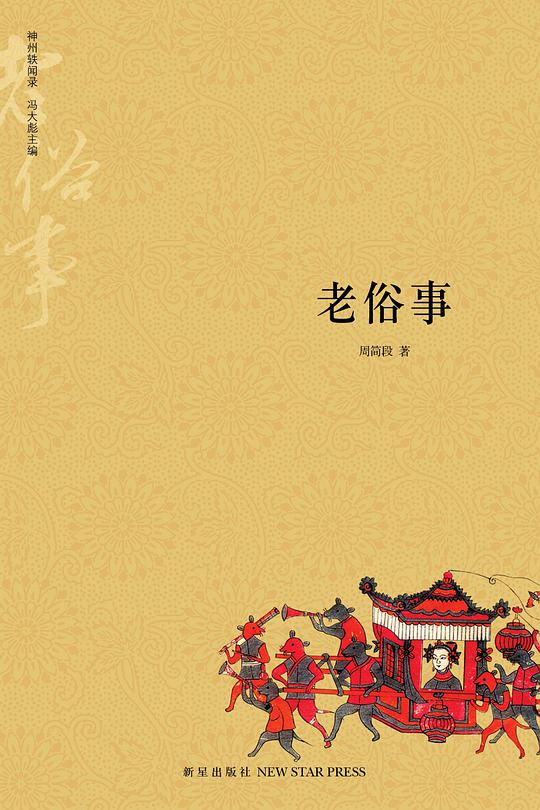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豆瓣
作者:
孙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
我在教书之余,陆续用了两年时间写出此书,总算告一段落了。编排目录后,才发现与预期的样子有别,然而生出来的孩子也只能如此。这本书,是对自己年轻时期的记忆的一次回溯,自然也有内心的寄托在。但要说有什么意义,却有些茫然,自己也理不清的。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 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等,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
现代以来的革命,自然有必然的逻辑,是社会矛盾与历史合力的结果。看秦汉以来的历史,我们似乎摆脱不了这样的巨变,那也是潮流所致。但回望那个血色的年代,我个人的经历快乐殊少,而是蒙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现在有谁歌颂“大跃进”与“文革”,内心总是不舒服的。那原因是自己做过奴隶。如果那样的革命是对的,我以为还是拒绝为好。它和李大钊、鲁迅那代人理解的革命殊远,也是对先贤的背叛。无奈,我们就曾在这样的背叛先贤的时代走过来的。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革命起伏不定的青年时代,结识了几个老人。他们在没有暖意的地方,给世间留下了温情。我见过许多“革命者”的面孔,一个个都很无趣,相反却在这些入世的隐者那里,见到了美丽的性灵。这些都神异地闪现在灰色的天幕上,给无聊的寒夜些许明快之色,才使我知道思想还可以这样开始,诗意的表达原来能够那样进行。那是怎样的有趣,我的冻僵的心似乎蠕活了。也恰是那样的遇合,有了我人生的变化。知道了应做什么,不做什么。虽然已晚,而望道无先后,其乐是一样的。
不错,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问题,汪曾祺那代人,比起鲁迅那代知识分子有退化的一面。比如中庸,比如不可避免的奴性等等。在那样严酷的时代,我们也不必苛求前人。在我看来,几千年来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具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倘能还有六朝的清峻,唐人的放达与宋明时期的幽婉,也是好的吧?我幼时受到的教育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居多,那是一种偏执。现在已经没有前人那样俊美的神采了,因为已经读不懂古人,对历史也知之甚少。
写这本书,是一次补课。许多陌生的资料给我诸多的提示。历史离我们并不远,而有许多存在要理解起来却很难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北大的氛围,失去了西南联大的语境,失去了与古人对话的通道。这些也许只有靠年轻人的重新启动才能解决。那么我的劳作,不过是多种尝试的一种,也算一种微弱的过渡,后继的人,会做得更好的。
现在学界的争论很多,派别林立,是不可免的生态。在我看来,无论左与右,失去了暖意的叙述,缺乏智性的文本,青年人是不会亲近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的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就审美而言,他们把传统的与域外现代的艺术结合得较好,或者说是融会贯通的。当代的作家,有此功夫的不多,汪曾祺等人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我沉入此中,不过是寻梦,以填补自己多年无聊的心境而已。
书在,已无需多言了。只是还想听听读者的意见,哪怕是相反的声音,也是好的。出版作品,不都是荣耀,更多的是漏出自己的原态,温吞与偏狭,固执和短视,都含在字里行间,巧饰是骗不了人的。如果因此而受到批评,知道自己的盲点,摆脱晦气,自然也是重新自省的机会。那么,我会更加的感激。
孙郁
2011年1月31日
现代以来的革命,自然有必然的逻辑,是社会矛盾与历史合力的结果。看秦汉以来的历史,我们似乎摆脱不了这样的巨变,那也是潮流所致。但回望那个血色的年代,我个人的经历快乐殊少,而是蒙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现在有谁歌颂“大跃进”与“文革”,内心总是不舒服的。那原因是自己做过奴隶。如果那样的革命是对的,我以为还是拒绝为好。它和李大钊、鲁迅那代人理解的革命殊远,也是对先贤的背叛。无奈,我们就曾在这样的背叛先贤的时代走过来的。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革命起伏不定的青年时代,结识了几个老人。他们在没有暖意的地方,给世间留下了温情。我见过许多“革命者”的面孔,一个个都很无趣,相反却在这些入世的隐者那里,见到了美丽的性灵。这些都神异地闪现在灰色的天幕上,给无聊的寒夜些许明快之色,才使我知道思想还可以这样开始,诗意的表达原来能够那样进行。那是怎样的有趣,我的冻僵的心似乎蠕活了。也恰是那样的遇合,有了我人生的变化。知道了应做什么,不做什么。虽然已晚,而望道无先后,其乐是一样的。
不错,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问题,汪曾祺那代人,比起鲁迅那代知识分子有退化的一面。比如中庸,比如不可避免的奴性等等。在那样严酷的时代,我们也不必苛求前人。在我看来,几千年来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具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倘能还有六朝的清峻,唐人的放达与宋明时期的幽婉,也是好的吧?我幼时受到的教育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居多,那是一种偏执。现在已经没有前人那样俊美的神采了,因为已经读不懂古人,对历史也知之甚少。
写这本书,是一次补课。许多陌生的资料给我诸多的提示。历史离我们并不远,而有许多存在要理解起来却很难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北大的氛围,失去了西南联大的语境,失去了与古人对话的通道。这些也许只有靠年轻人的重新启动才能解决。那么我的劳作,不过是多种尝试的一种,也算一种微弱的过渡,后继的人,会做得更好的。
现在学界的争论很多,派别林立,是不可免的生态。在我看来,无论左与右,失去了暖意的叙述,缺乏智性的文本,青年人是不会亲近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的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就审美而言,他们把传统的与域外现代的艺术结合得较好,或者说是融会贯通的。当代的作家,有此功夫的不多,汪曾祺等人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我沉入此中,不过是寻梦,以填补自己多年无聊的心境而已。
书在,已无需多言了。只是还想听听读者的意见,哪怕是相反的声音,也是好的。出版作品,不都是荣耀,更多的是漏出自己的原态,温吞与偏狭,固执和短视,都含在字里行间,巧饰是骗不了人的。如果因此而受到批评,知道自己的盲点,摆脱晦气,自然也是重新自省的机会。那么,我会更加的感激。
孙郁
201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