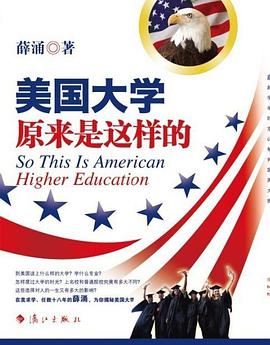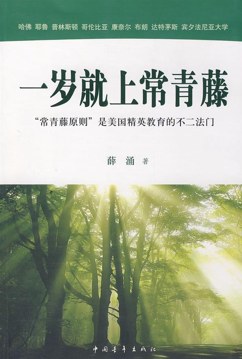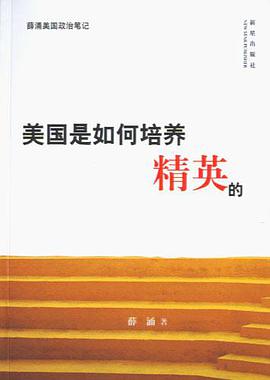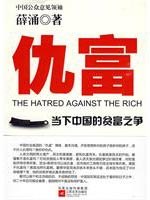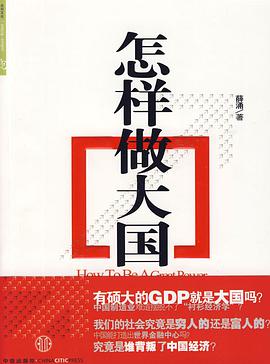2009年一开始,我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一岁就上常青藤》,相信春节一过就能和读者见面。此书大概也界定了我这一年的个人生活。
此书的目的,并不是真要把还没有学会说话的一岁孩子赶到常青藤去读大学。常青藤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精英的教育,也象征着某种教育理想。 “一岁就上常青藤”的意思,是从小在孩子的教育中追求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即塑造一个全面的人(well-rounded person)。在这一理想下,教育的使命是唤醒孩子内心的自觉,让他们产生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形成自我、确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孩子不是在权威的喝令中发育,而是为自己的内心冲动所驱使。这和我们从小让孩子似懂非懂地背古诗、甚至读经、在大人筑造好的模子中生长的盆景式教育,实在有天壤之别。
我的小女在美国土生土长,如今已经九岁。我们对她的教育方法,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根据我个人观察,会培养孩子的美国家长,从小的教育方式也和我们小时候所领教的那一套不一样。当然,我也经常翻阅一些教育方面的研究、报道,最后把自己养孩子的亲身经验、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乃至初步的教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了这本小书。
在美国,越是有教养的家长,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淡化自己的权威性,增强和孩子的对话性。有位中国人曾观察到:这些美国家长和自己的孩子说话时,经常蹲下来,把自己的脸降到和孩子的脸同一个高度。这种物理上的平等,导致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几年前,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经过大量观察研究后出版了一本书,叫《不平等的童年》。她发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有事总和孩子商量,大家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孩子也习惯于提问,争论。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和孩子讲话的语言则非常武断权威,常用的词汇是“去干这个”、“别干这个”、“不行”,“闭嘴”等等。这两种家庭的孩子,前者从小习惯了讨论问题,长大后遇到事情善于协商、谈判、说理、争论、甚至讨价还价。后者从小在和家长的关系中就没有回过嘴,长大后常常沉默寡言,万事等人家吩咐,没有自己的主意,甚至连提问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人,不适合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打交道。这成为他们在教育和事业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这一研究,对中国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你不能说:孩子不到懂事的时候,有些道理先让他记住,以后自然就懂了。要知道,强迫记住的道理仅仅是训戒,而不是道理。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成为道理。孩子如果从小习惯于遵循自己并不懂的训戒,对大人的观点不质疑、不讨论,那么长大以后就不知道根据道理还组织自己的生活、贡献于社会。
我在讨论中国大学的改革时曾经指出,常青藤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是讨论班(seminar):师生围坐在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而不是教授讲、学生听。中国的大学应该学习这种讨论班。后来几位国内的研究生给我写信说:“现在讨论班也有。但是效果还不如大课。主要是教授习惯了满堂灌,不知道怎么激发学生讨论,学生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白白浪费时间。”这其实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常青藤教育,不能等上大学才开始,而要从小开始,否则到了大学,有讨论班也手足无措。九年来,我一直坚持以讨论的形式教育女儿。还记得她八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边给她摸背边哄她睡觉时,两人还讨论了一通柏拉图的“理念型”的概念,虽然她并不知道柏拉图是谁。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最著名的电视政治节目主持人Tim Russert突然去世。我正对着电视看悼念新闻,女儿跑过来问:“他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谈论他?”我对女儿说:“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问问题。他比任何人都会问问题。所以,每次总统大选,人们都要听他问问题、让他代表大家问问题。现在总统还没有选出来,他却去世了。世界在最需要问问题的时候,最会问问题的人没有了。这就是人们谈论他的原因。看看,问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你用一辈子的时间能学会象他那样问问题,你就很了不起了?”女儿恍然有悟。父女之间又开始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要问问题、如何问问题的“讨论班”。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常青藤教育。你不用送孩子去哈佛耶鲁,每个家长都可以从自己家里开始。我把自己的经验老实地展示给大家,期待着读者的提问、质疑、争辩、和批判。或者说,我希望随着我的书的出版,今年能和读者就这些问题开始一个跨越太平洋的“讨论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