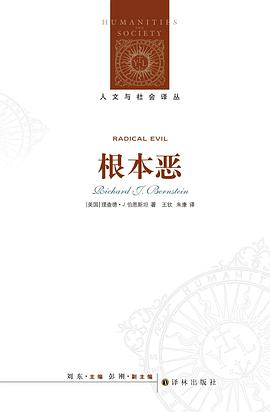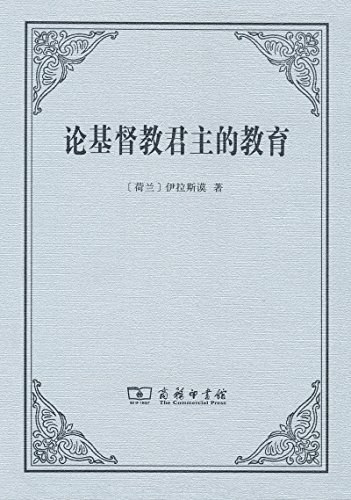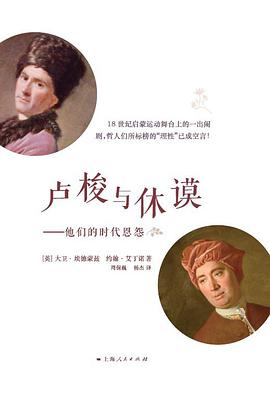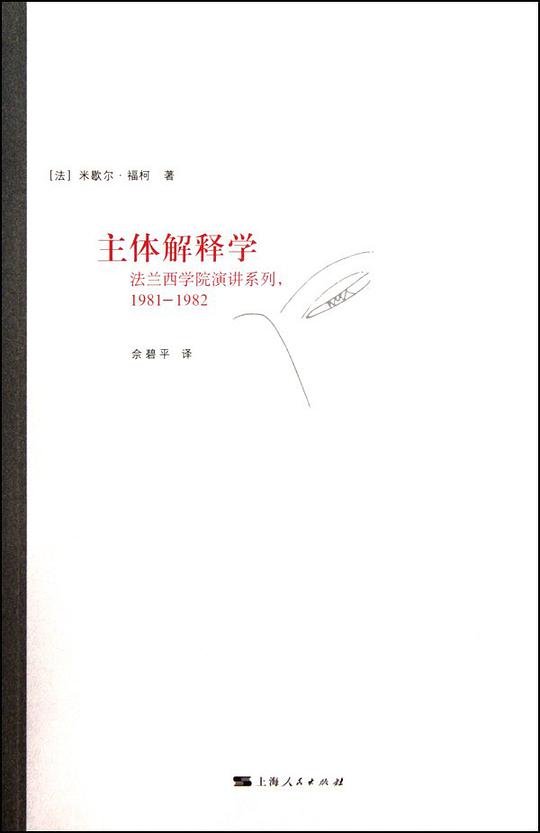被拯救的威尼斯 豆瓣
La Venise sauvée
8.8 (27 个评分)
作者:
[法]西蒙娜·薇依
译者:
吴雅凌
华夏出版社
2019
- 3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20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思想大师。《被拯救的威尼斯》是西蒙娜•薇依生平写过的唯一一部悲剧。
《被拯救的威尼斯》的故事取材于圣雷拉尔修士所记载的、一桩发生在1618年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西班牙人谋反威尼斯共和国事件”。十七世纪初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盛极一时,为达到将威尼斯共和国收归治下的目的,暗中策划了一次谋反行动。时值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夕,欧洲各国均设有常备雇佣军。西班牙人收买大部分驻威尼斯的雇佣军和若干外国军官,计划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夜突袭威尼斯。行动计划的指挥之一加斐尔出于怜悯向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告密,致使行动败露,所有谋反者当夜被处以死刑。加斐尔本人被驱逐出威尼斯。
这部悲剧一以贯之地围绕薇依始终关注的人类基本问题。这两句话可为佐证:“怜悯从根本上是属神的品质;不存在属人的怜悯;怜悯暗示了某种无尽的距离;对邻近的人事不可能有同情。”“自古希腊以来,第一次重拾完美的英雄这一悲剧传统。”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两句话亦是理解和思考《被拯救的威尼斯》的起点。
《被拯救的威尼斯》的故事取材于圣雷拉尔修士所记载的、一桩发生在1618年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西班牙人谋反威尼斯共和国事件”。十七世纪初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盛极一时,为达到将威尼斯共和国收归治下的目的,暗中策划了一次谋反行动。时值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夕,欧洲各国均设有常备雇佣军。西班牙人收买大部分驻威尼斯的雇佣军和若干外国军官,计划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夜突袭威尼斯。行动计划的指挥之一加斐尔出于怜悯向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告密,致使行动败露,所有谋反者当夜被处以死刑。加斐尔本人被驱逐出威尼斯。
这部悲剧一以贯之地围绕薇依始终关注的人类基本问题。这两句话可为佐证:“怜悯从根本上是属神的品质;不存在属人的怜悯;怜悯暗示了某种无尽的距离;对邻近的人事不可能有同情。”“自古希腊以来,第一次重拾完美的英雄这一悲剧传统。”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两句话亦是理解和思考《被拯救的威尼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