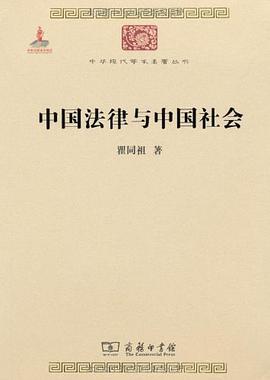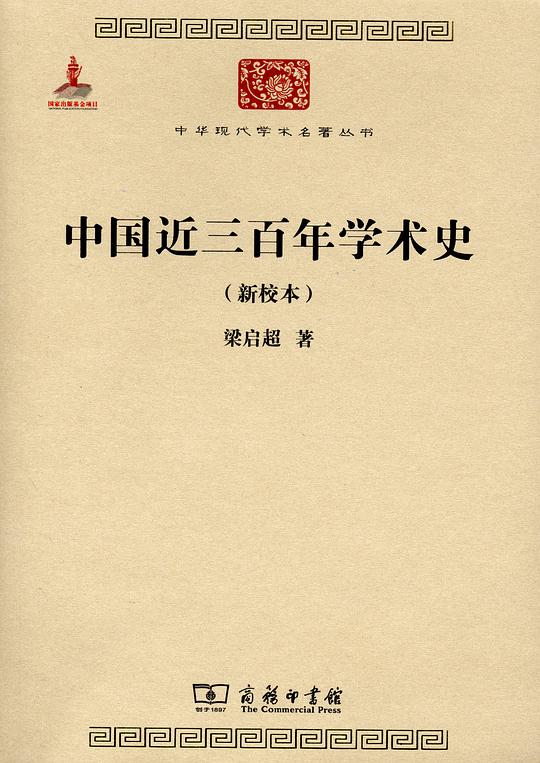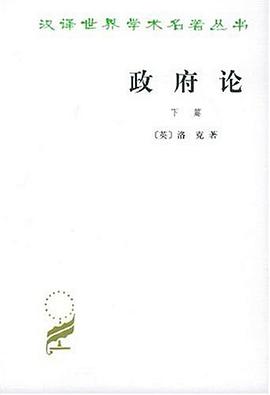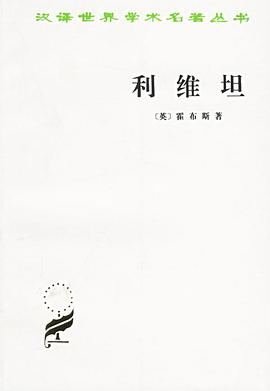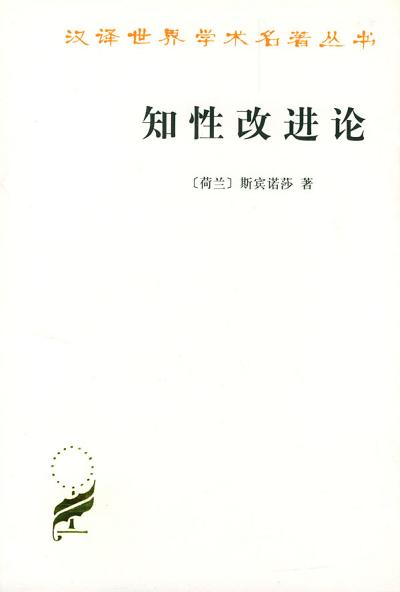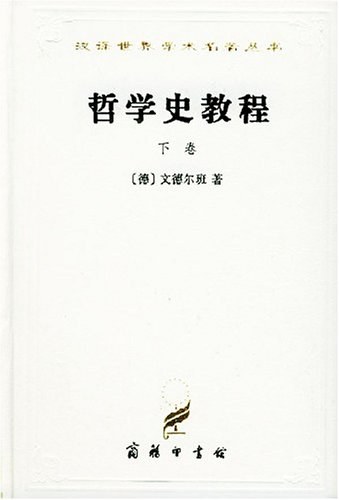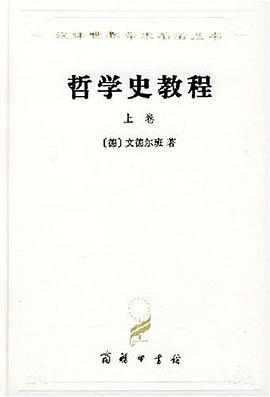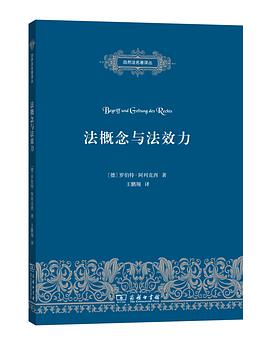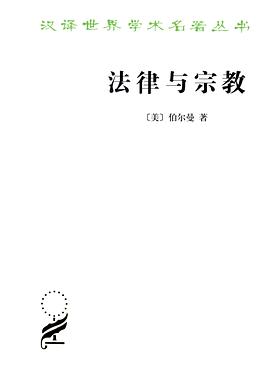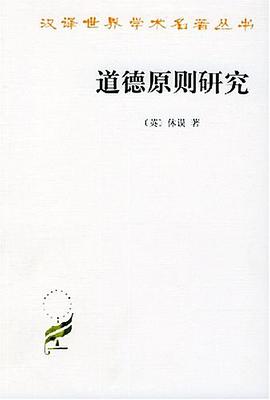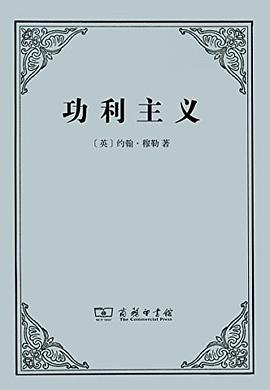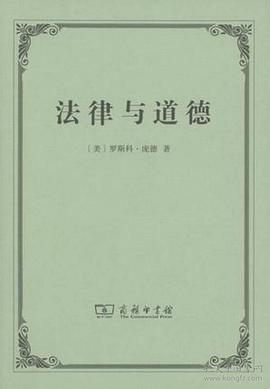商务印书馆
司法过程的性质 豆瓣
作者:
(美)本杰明•卡多佐
译者:
苏力
商务印书馆
1998
- 11
《司法过程的性质》最初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所作的一个演讲,为的是纪念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已经去世的毕业生——阿瑟·P.麦金斯特里。这部讲演不仅是卡多佐的第一部用心之作,而且是卡多佐对自己多年担任法官的经验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美国自霍姆斯以来形成的实用主义司法哲学的一个系统的理论化阐述。尽管该书是一个讲演,篇幅不长,语言简洁,但是其视野开阔,含义深邃。
《司法过程的性质》根据192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社的英文本翻译;原书没有索引,参照Margaret E.Hall 1947年编辑的由Fallon法律著作出版公司出版的《卡多佐文选》的索引,希望对部分读者能有所便利。
《司法过程的性质》根据192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社的英文本翻译;原书没有索引,参照Margaret E.Hall 1947年编辑的由Fallon法律著作出版公司出版的《卡多佐文选》的索引,希望对部分读者能有所便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 豆瓣
8.8 (5 个评分)
作者:
梁启超
/
校注 陆胤
…
译者:
夏晓虹
/
陆胤 校订
商务印书馆
2011
本书原为1923年秋至1924年春夏间,梁启超在清华等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成书后共分十六讲。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题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华学校讲义”一册,现存第一至十二讲(第十二讲未完)内容,经过与当时听讲者回忆的对照,应即为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原本。(以下简称“讲义本”)
该书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计有:
(一)《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即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原载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二)《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即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部分,原载1924年3月2日至6日《晨报副镌》。
(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相当于单行本第十三至十五讲,原载1924年6月至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13、15-18号。
(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包含第一至十二讲全部内容,自1924年4月(实则7月以后)至1925年10月(实则11月以后),连载于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第3-8期;经比对,该种即为转载前述“清华学校讲义”本。(上述四种,以下简称“报刊本”)
1926年7月,上海民志书店刊行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首个单行本,至1929年10月已发行至第四版(以下简称“民志本”)。1936年,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专集”部分收入该书,并将报刊本及民志本所用新式标点改为旧式断句,成为此后该书较为通行的版本(以下简称“《合集》本”)。可能由于成书仓促,这两种单行本均有较多印刷错误。
“清华学校讲义”为本书最初版本,亦可视为民志、《合集》两种单行本的母本。早先发表于《东方杂志》等报刊的部分,在收入民志、《合集》二本时稍有增删,但整体内容变化不大。讲义本、报刊本虽为梁氏未定稿,较之后出单行本,错误反而较少。故本次校订,遵循早出讲义本、报刊本为先的原则:
(一)第一讲至第十二讲,见于“清华学校讲义”的部分,以讲义本为底本,参校报刊本及民志、《合集》二本;国图藏讲义本有缺页,补以《史地学报》转载本。
(二)第十三讲至十五讲,见于《东方杂志》的部分,以报刊本为底本,参校民志、《合集》二本。
(三)其余部分,则以较为完整的《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
具体凡例如下:
1、底本无误者,参校本有异同一般亦不出校记。
2、底本及参校本皆误者,直接在文中修正:拟改之字以[ ]表示,拟增之字以【 】表示,衍字以{ }表示。明显错字、借字,如“已”、“己”、“巳”混用,“很”作“狠”,“著”作“箸”之类,径行在文中改正。
3、参考底本所用标点,转换为现行标点符号;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字。底本以“□”表示待补字,“(?)”表示存疑,连续星号(*)表示段落区隔,均予保留。
4、为存梁氏定本面貌,凡后出单行本对讲义本、报刊本有大段增删处,以及章节划分、章节名有更改处,仍依《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并在校记中说明。但该部分个别字句的增删,则以讲义本、报刊本为主。
5、该书征引前人著作,或转引他书,或仅凭记忆,或隐括大意,与原书字句往往相异。为存梁氏著作风格,除非影响文义或出现知识性错误之处,其他引文与原书字句有出入者,一般不加校改。
该书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计有:
(一)《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即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原载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二)《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即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部分,原载1924年3月2日至6日《晨报副镌》。
(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相当于单行本第十三至十五讲,原载1924年6月至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13、15-18号。
(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包含第一至十二讲全部内容,自1924年4月(实则7月以后)至1925年10月(实则11月以后),连载于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第3-8期;经比对,该种即为转载前述“清华学校讲义”本。(上述四种,以下简称“报刊本”)
1926年7月,上海民志书店刊行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首个单行本,至1929年10月已发行至第四版(以下简称“民志本”)。1936年,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专集”部分收入该书,并将报刊本及民志本所用新式标点改为旧式断句,成为此后该书较为通行的版本(以下简称“《合集》本”)。可能由于成书仓促,这两种单行本均有较多印刷错误。
“清华学校讲义”为本书最初版本,亦可视为民志、《合集》两种单行本的母本。早先发表于《东方杂志》等报刊的部分,在收入民志、《合集》二本时稍有增删,但整体内容变化不大。讲义本、报刊本虽为梁氏未定稿,较之后出单行本,错误反而较少。故本次校订,遵循早出讲义本、报刊本为先的原则:
(一)第一讲至第十二讲,见于“清华学校讲义”的部分,以讲义本为底本,参校报刊本及民志、《合集》二本;国图藏讲义本有缺页,补以《史地学报》转载本。
(二)第十三讲至十五讲,见于《东方杂志》的部分,以报刊本为底本,参校民志、《合集》二本。
(三)其余部分,则以较为完整的《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
具体凡例如下:
1、底本无误者,参校本有异同一般亦不出校记。
2、底本及参校本皆误者,直接在文中修正:拟改之字以[ ]表示,拟增之字以【 】表示,衍字以{ }表示。明显错字、借字,如“已”、“己”、“巳”混用,“很”作“狠”,“著”作“箸”之类,径行在文中改正。
3、参考底本所用标点,转换为现行标点符号;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字。底本以“□”表示待补字,“(?)”表示存疑,连续星号(*)表示段落区隔,均予保留。
4、为存梁氏定本面貌,凡后出单行本对讲义本、报刊本有大段增删处,以及章节划分、章节名有更改处,仍依《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并在校记中说明。但该部分个别字句的增删,则以讲义本、报刊本为主。
5、该书征引前人著作,或转引他书,或仅凭记忆,或隐括大意,与原书字句往往相异。为存梁氏著作风格,除非影响文义或出现知识性错误之处,其他引文与原书字句有出入者,一般不加校改。
利维坦 豆瓣 Goodreads
Leviathan
8.8 (40 个评分)
作者:
[英国] 霍布斯
译者:
黎思复
/
黎廷弼
商务印书馆
1985
- 9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腐朽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地志,服从他的判断。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领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知性改进论 豆瓣
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Et de via, Qua Optime in Veram Rerum Cognitionem Dirigitur
8.0 (10 个评分)
作者:
[荷兰] 巴鲁赫·斯宾诺莎
译者:
贺麟
商务印书馆
1960
- 2
斯宾诺莎(1632—1677)是荷兰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理性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知性改进论》是斯宾诺莎最早的一部著作,篇幅不大,副标题为“并论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斯宾诺莎在书中探讨了寻求知识的途径和方法,指出真理和实在的系统一贯性,并力图把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力学和数学的精神推广应用到研究存在的认识的整个领域。
新系统及其说明 豆瓣
Systeme Nouveau et les Eclaircissements de ce Systeme
作者:
[德国]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译者:
陈修斋
商务印书馆
2002
- 11
本书内容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663-1671年的“哲学作品”;第二部分标明为1677-1702年“莱布尼茨尼反对笛卡尔及笛卡尔学派”;第三部分则为1684-1703年的“哲学论文”。本书各篇为第三部分的后半即Ⅴ至Ⅷ各组,其中Ⅴ包括本书中“新系统”本文直至“新系统说明”各篇只是原书“新系统初稿”是放在“新系统”正文之前,而本译则移置其后;Ⅶ包含“说明(四)”至“说明(六)”;包含“说明(七)”至“说明(八)”。
第一哲学沉思集 豆瓣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9.2 (39 个评分)
作者:
[法] 笛卡尔
译者:
庞景仁
商务印书馆
1986
- 6
《第一哲学的沉思》是笛卡尔运用与《谈谈方法》提出的方法原则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
笛卡尔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1628年写成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这部著作规定了笛卡尔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他后来一切哲学奥秘的真正发源地。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尔不但将追求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从而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而且还确定了从方法入手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途径。他认为,关于精神、物质的形而上学知识是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但是要获得可靠的形而上学知识,必须首先确定获得这些知识的正确方法,这是一切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关键。笛卡尔后来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第一哲学的沉思》等也遵循了同样的思路。比如《谈谈方法》(全名《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的书名已经清楚表明了该书的主旨;[②]而《第一哲学的沉思》按笛卡尔所说,则是运用与《谈谈方法》同样的方法原则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
笛卡尔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1628年写成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这部著作规定了笛卡尔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他后来一切哲学奥秘的真正发源地。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尔不但将追求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从而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而且还确定了从方法入手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途径。他认为,关于精神、物质的形而上学知识是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但是要获得可靠的形而上学知识,必须首先确定获得这些知识的正确方法,这是一切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关键。笛卡尔后来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第一哲学的沉思》等也遵循了同样的思路。比如《谈谈方法》(全名《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的书名已经清楚表明了该书的主旨;[②]而《第一哲学的沉思》按笛卡尔所说,则是运用与《谈谈方法》同样的方法原则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
贫困与饥荒 豆瓣 Goodreads Eggplant.place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8.9 (19 个评分)
作者:
[印度] 阿马蒂亚·森
译者:
王宇
/
王文玉
商务印书馆
2004
- 1
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要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分析方法。那些关于穷人的冗长啰嗦的经院研究,那些使用《李尔王》中诸如“居无定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等绘画般的描述,难免会使人感到厌烦。有些事情,就像李尔王告诉瞎子格洛斯特的那样,“一个人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的确,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目了然。
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目前,可供使用的贫穷识别方法有许多种(如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相对贫困等),不过,每一种方法中都还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要从整体上描绘贫困,还必须超越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因为,要在贫困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贫困的整体画面,“加总”问题将无法回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需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在近期关于饥饿现象原因的研究中,贫困的起因具有特殊重要性。
这本专著所关注的正是这些问题,本书的重点是关于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第1章从一般意义上引入了基本方法,包括对“权利体系” 分析。之所以在详细论述贫穷概念之前就进行这一分析,是因为“权利方法”是这本著作的核心。第2章和第3章研究了关于贫困的概念和度量问题。第4章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饥饿这一特殊问题。第5章分析“权利方法”。随后几章分析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案例: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第6章)、1973至 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第7章)、70年代早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第8章)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第9章);第10章是关于“权利方法”的总结,即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利体系的联系。
本书有四个附录。附录A给出了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换权利的公式化分析。附录B借助于一些模型说明了“交换权利失败” (failure of exchange entitlement)在饥荒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附录C研究了贫困的度量问题,详细阐明了已经得到应用和已经提出的各种度量方法。最后,附录D以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为例,分析了饥荒死亡人口的分布问题。
本书原本是为国际劳工局世界就业计划(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of ILO)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耐心,因为本书的完成比我原来的设想要迟得多。我也衷心感谢费利克斯·波克特(Felix Paukert)等人与我关于收入分配和就业计划的有益讨论。朱迪思·海尔(Judith Heyer)和乔斯莱恩·肯奇(Jocelyn Kynch)对本书初稿的评论也使我受益良多。很多学者都给我提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他们是:莫胡狄恩·阿拉姆基尔(Mohuddin Alam-gir)、苏底尔·阿南德(Sudhir Anand)、阿塞特·布赫塔克基亚(Asit Bhattacharya)、罗伯特·卡森(Robert Cassen)、迪盘卡·查第尔基(Dipankar Chatterjee)、普拉米特·肖德赫利(Pramit Chaudhuri)、阿米亚·达斯哥普塔(Amiya Dasgupta)、梅纳德·德塞(Meghnad Desai)、约翰·弗莱明(John Flemming)、马戴恩古普尔·古什(Madangopal Ghosh)、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泰仑斯·戈曼(Terence Gorman)、凯斯·戈利芬(Keith Griffin)、卡尔·哈米尔顿(Carl Hamilton)、鲁戈·哈弋(Roger Hay)、朱利斯·霍尔特(Julius Holt)、雷弗·约翰森(Leif Johansen)、J.克里西纳莫第(J.Krishnamurti)、穆库·马加姆达(Mukul Majumdar)、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约翰·缪尔鲍尔(John Muellbauer)、苏奇·佩恩(Suzy Paine)、戴比达斯·雷(Debidas Ray)、戴布拉·雷(Debrai Ray)、萨米尔·雷(Samir Ray)、塔班·雷坎德胡利(Tapan Raychaudhuri)、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乔恩·罗宾逊(Joan RobinSon)、苏曼·萨卡(Suman Sarkar)、约翰·希曼(John Seaman)、里翰·索布罕(Rehan Sobhan)、K.苏德拉姆(K.Sundaram)、加罗斯拉夫·瓦尼克(Jaroslav Vanek)和亨利·万(Henry Wan)等。
本书中还引用了我早期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73、1976)、《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1976、1977),《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6)、《剑桥经济学月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月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经济学文献月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980)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附录A到附录C,都使用了一些数学概念和符号,但是,本书的分析基本上是非公式化的。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不过、即使不参阅附录,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包括案例研究)也不会有任何困难。由于本书的主题非常重要,我将尽可能使其通俗一些。可以不谦虚地说,在这本专题著作中,我所作出的分析是相当有实际意义的。
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目前,可供使用的贫穷识别方法有许多种(如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相对贫困等),不过,每一种方法中都还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要从整体上描绘贫困,还必须超越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因为,要在贫困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贫困的整体画面,“加总”问题将无法回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需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在近期关于饥饿现象原因的研究中,贫困的起因具有特殊重要性。
这本专著所关注的正是这些问题,本书的重点是关于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第1章从一般意义上引入了基本方法,包括对“权利体系” 分析。之所以在详细论述贫穷概念之前就进行这一分析,是因为“权利方法”是这本著作的核心。第2章和第3章研究了关于贫困的概念和度量问题。第4章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饥饿这一特殊问题。第5章分析“权利方法”。随后几章分析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案例: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第6章)、1973至 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第7章)、70年代早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第8章)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第9章);第10章是关于“权利方法”的总结,即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利体系的联系。
本书有四个附录。附录A给出了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换权利的公式化分析。附录B借助于一些模型说明了“交换权利失败” (failure of exchange entitlement)在饥荒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附录C研究了贫困的度量问题,详细阐明了已经得到应用和已经提出的各种度量方法。最后,附录D以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为例,分析了饥荒死亡人口的分布问题。
本书原本是为国际劳工局世界就业计划(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of ILO)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耐心,因为本书的完成比我原来的设想要迟得多。我也衷心感谢费利克斯·波克特(Felix Paukert)等人与我关于收入分配和就业计划的有益讨论。朱迪思·海尔(Judith Heyer)和乔斯莱恩·肯奇(Jocelyn Kynch)对本书初稿的评论也使我受益良多。很多学者都给我提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他们是:莫胡狄恩·阿拉姆基尔(Mohuddin Alam-gir)、苏底尔·阿南德(Sudhir Anand)、阿塞特·布赫塔克基亚(Asit Bhattacharya)、罗伯特·卡森(Robert Cassen)、迪盘卡·查第尔基(Dipankar Chatterjee)、普拉米特·肖德赫利(Pramit Chaudhuri)、阿米亚·达斯哥普塔(Amiya Dasgupta)、梅纳德·德塞(Meghnad Desai)、约翰·弗莱明(John Flemming)、马戴恩古普尔·古什(Madangopal Ghosh)、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泰仑斯·戈曼(Terence Gorman)、凯斯·戈利芬(Keith Griffin)、卡尔·哈米尔顿(Carl Hamilton)、鲁戈·哈弋(Roger Hay)、朱利斯·霍尔特(Julius Holt)、雷弗·约翰森(Leif Johansen)、J.克里西纳莫第(J.Krishnamurti)、穆库·马加姆达(Mukul Majumdar)、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约翰·缪尔鲍尔(John Muellbauer)、苏奇·佩恩(Suzy Paine)、戴比达斯·雷(Debidas Ray)、戴布拉·雷(Debrai Ray)、萨米尔·雷(Samir Ray)、塔班·雷坎德胡利(Tapan Raychaudhuri)、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乔恩·罗宾逊(Joan RobinSon)、苏曼·萨卡(Suman Sarkar)、约翰·希曼(John Seaman)、里翰·索布罕(Rehan Sobhan)、K.苏德拉姆(K.Sundaram)、加罗斯拉夫·瓦尼克(Jaroslav Vanek)和亨利·万(Henry Wan)等。
本书中还引用了我早期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73、1976)、《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1976、1977),《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6)、《剑桥经济学月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月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经济学文献月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980)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附录A到附录C,都使用了一些数学概念和符号,但是,本书的分析基本上是非公式化的。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不过、即使不参阅附录,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包括案例研究)也不会有任何困难。由于本书的主题非常重要,我将尽可能使其通俗一些。可以不谦虚地说,在这本专题著作中,我所作出的分析是相当有实际意义的。
哲学史教程(下卷) 豆瓣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phie
作者:
文德尔班
译者:
罗达仁
商务印书馆
1997
- 2
《哲学史教程》(下)(精装)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正如甚至连这种阐述的外部形式也表明的那样,着重点就放在从哲学的观点看最有份量的东西的发展上,即放在问题和概念的历史上。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发展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我们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产生于各种思想路线,而这些思想路线在历史上的相互交织便是我研究的特定的对象。我确信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如果说,在此书的阐述中,看起来古代部分占去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这是基于这种信念:如对人类理智的现实作历史性的了解,那么,用希腊精神从自然界和人生的具体现实中所获得的种种概念来陶冶锻炼,就要比自此以后所有人们思考过的东西更为重要——康德哲学除外。任务这样确定了,就必须割爱;关于这点,没有人比我更为难过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容许对哲学家的品格作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这只有当在概念的结合和转化过程中他们的品格可以作为原因因素而起积极作用时才可能触及。为了有利于更好地深入洞察心灵发展过程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在此不得不牺牲推动哲学发展的伟大人物的个人风格中的艺术魅力,不得不牺牲赋予学术讲演以及赋予哲学史更广泛的阐述的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
哲学史教程(上卷) 豆瓣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phie
作者:
(德)文德尔班
译者:
罗达仁
商务印书馆
1987
- 4
《哲学史教程》(上)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读者不可将此书和纲要之类混淆起来。纲要之类的书有时很可能就是从一般哲学史的讲稿中整理出来的。我现在献给读者的是一部严肃的教科书。在这《哲学史教程》(上)里,我打算全面而精炼地描述欧洲哲学种种观念的演变,其目的在于表明:我们现在对宇宙和人生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理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这个目的决定了这《哲学史教程》(上)的整个形式。据此,我们研究的文史依据和传记、文献资料都必然地限制在最小范围,选材也只限于能为进一步钻研的读者获得最丰富的原始资料而开辟道路。哲学家本人的论述,也只有在那些论述能提供在思想上有持久价值的论证或基本原理时,才扼要地加以引证。除此之外,作者为了支持某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也偶尔引用了原著一些段落。选材总着眼于个别思想家所提出的既新颖而又富有成果的东西;而对于那些纯属于个人的思想倾向,虽然作为学术研究确有可取之处,但不能引起哲学兴味者,最多也不过略略提及而已。
法律与宗教 豆瓣
作者:
[美] 伯尔曼
译者:
梁治平
商务印书馆
2012
- 11
该书的英文原书出版于1974年,H.J.伯尔曼这部《法律与宗教》是极富洞见的一本书。提出了如下问题:生活的意义何在,我们正去向何方?本书是一部演讲集,它意在论断和诘难,而非详细论证。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尽管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紧张,但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一方。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
本书附录所收三篇文字都与千禧年有关,附录一重点在《法律与宗教》结尾处提及的人类共同的法律与宗教;附录二立于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谈西方法律传统和世界法;附录三是一篇接受中文媒体的访谈,因此与中国有更多关联。
本书附录所收三篇文字都与千禧年有关,附录一重点在《法律与宗教》结尾处提及的人类共同的法律与宗教;附录二立于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谈西方法律传统和世界法;附录三是一篇接受中文媒体的访谈,因此与中国有更多关联。
历史的地理枢纽 豆瓣
作者:
(英)麦金德
译者:
林尔蔚
/
陈江
商务印书馆
2010
- 10
本书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文章虽然都不很长,影响却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后者,我们就以它作为书名。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份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则影响到世界政治。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六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