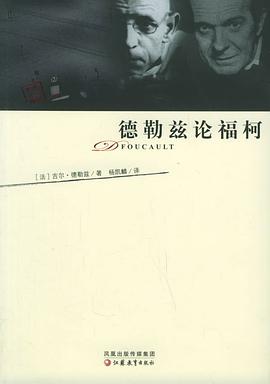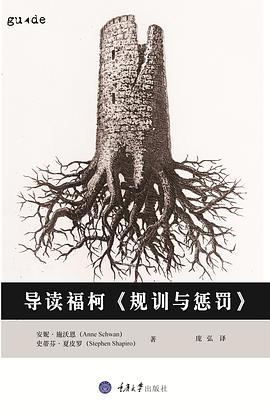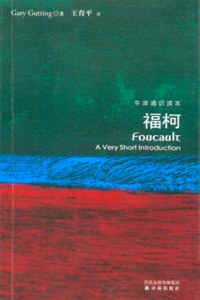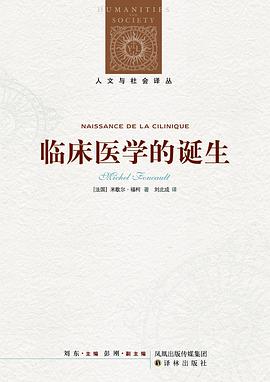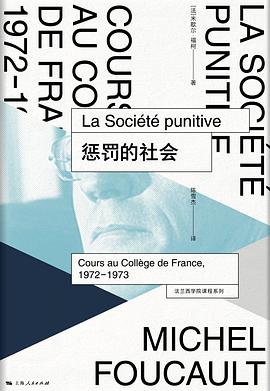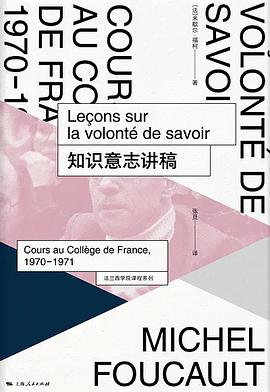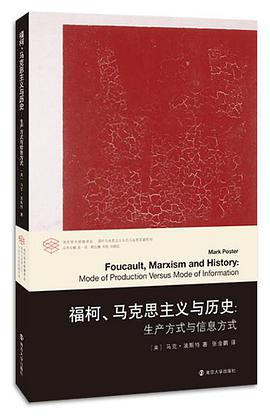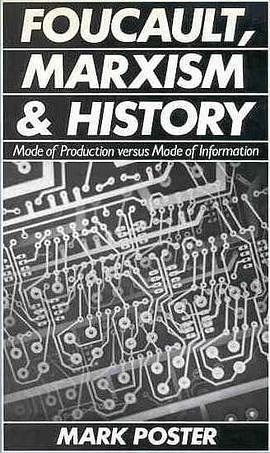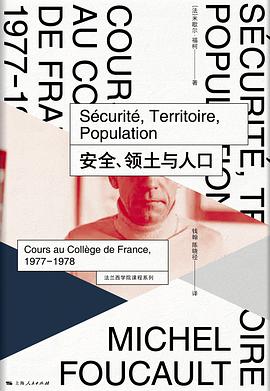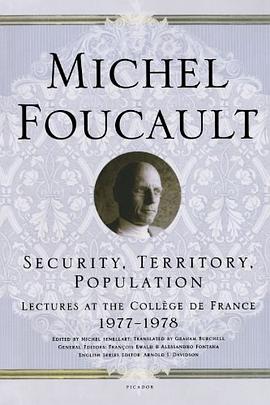雷蒙·鲁塞尔 豆瓣
Raymond Roussel
作者:
[法] 米歇尔·福柯
译者:
汤明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4
雷蒙·鲁塞尔的语言是一个太阳,劈开了万物。——米歇尔·福柯
******内容简介*******
本书是福柯唯一一本文学研究著作,一部被他称为“非常私人化”的作品。当20世纪50年代,福柯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书店与鲁塞尔的作品不期而遇时,雷蒙·鲁塞尔只 是一名与普鲁斯特同时代的不起眼的边缘作家、一名“实验派作家”。他的作品不遵循任何文学理论,也不从属于任何文学流派。
在本书中,通过对鲁塞尔文学作品的解读,福柯阐释了语言与死亡的关系。在福柯看来,文学的真正任务不是表现或者反映“物”的现实性,而是要展现闪光和扩散的过程,创造出一个语言急于进入的“空白”。本书充分地体现了福柯对语言的深刻思考和批判,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词与物》的前传。
******内容简介*******
本书是福柯唯一一本文学研究著作,一部被他称为“非常私人化”的作品。当20世纪50年代,福柯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书店与鲁塞尔的作品不期而遇时,雷蒙·鲁塞尔只 是一名与普鲁斯特同时代的不起眼的边缘作家、一名“实验派作家”。他的作品不遵循任何文学理论,也不从属于任何文学流派。
在本书中,通过对鲁塞尔文学作品的解读,福柯阐释了语言与死亡的关系。在福柯看来,文学的真正任务不是表现或者反映“物”的现实性,而是要展现闪光和扩散的过程,创造出一个语言急于进入的“空白”。本书充分地体现了福柯对语言的深刻思考和批判,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词与物》的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