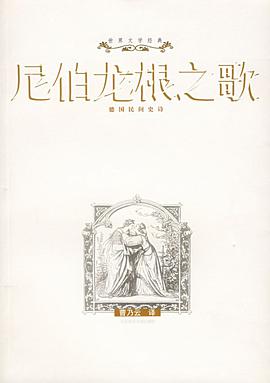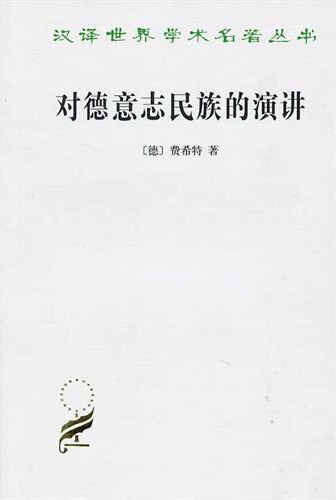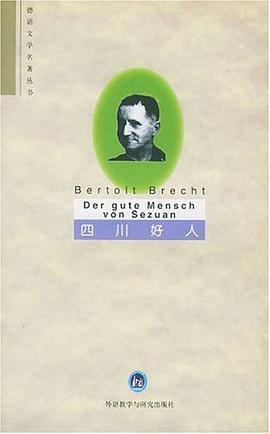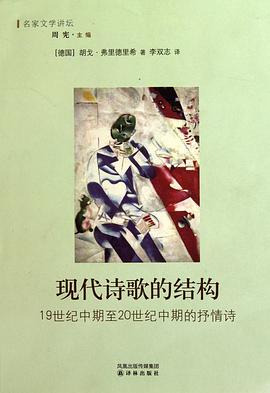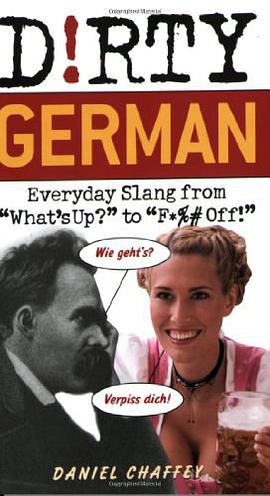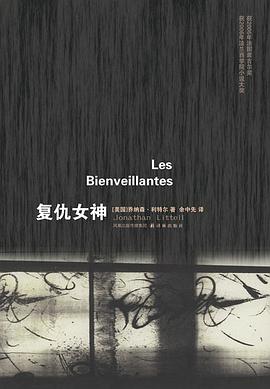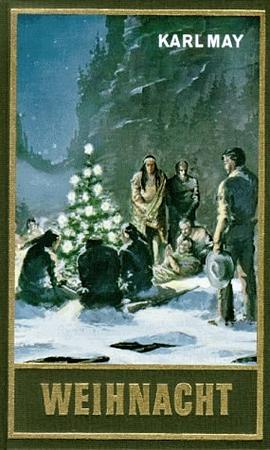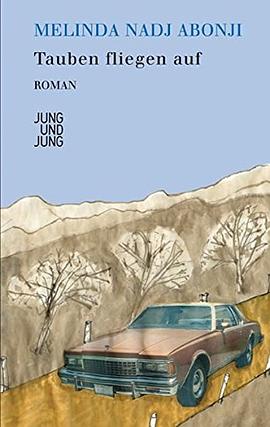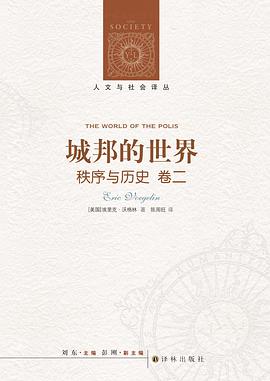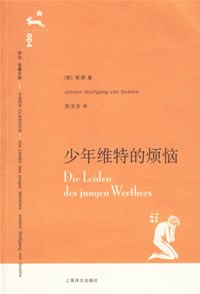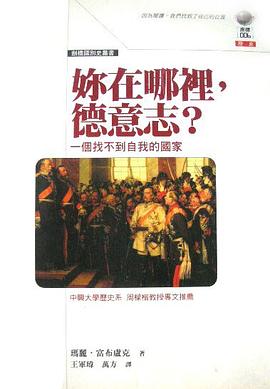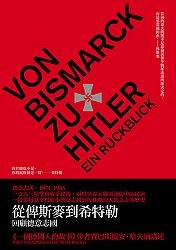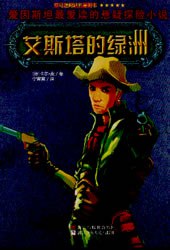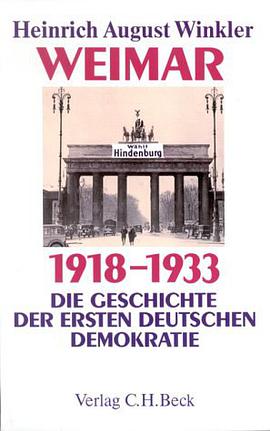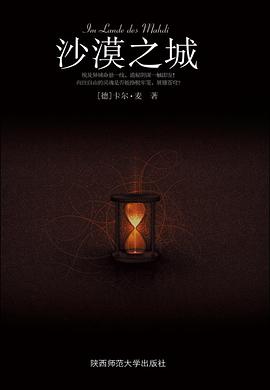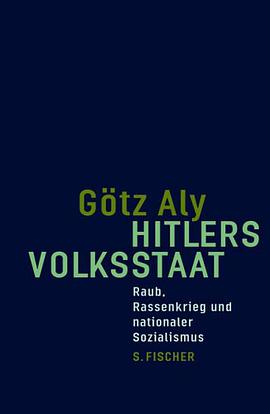德國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豆瓣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作者:
(德) 费希特
译者:
梁志学
商务印书馆
2010
- 10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内容简介:费希特的这部作品是他从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在柏林所作的十四次演讲,发表于1808年5月中旬,由于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大家认为是一部世界名著而载入史册。不过,对于它的包罗宏富的内容,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当中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于它的基本观点的评价也就往往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中文版问世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初步理解和研究结果,扼要地向我国读者谈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从当时欧洲政局的急剧变化和费希特哲学的现实使命来看,这部著作是如何形成的?其次,它究竟包含着哪些基本观点?它们是如何表述出来的?它们在什么限度内是正确的?以及最后它的历史命运如何?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它?
四川好人 豆瓣
作者: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译者:
吴麟绶 注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 1
《四川好人》是布莱希特创作的一出寓意剧。首演于1943年。说的是两千年来世上好人难以立足,民怨沸腾,因此三位神仙下凡来到人间寻访好人。但他们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不愿给他们提供栖身之地。只有好心的妓女沈德收留了他们。第二天清晨,三位神仙以付住宿费的名义给了沈德一千多银元。这样,沈德再不必以卖身为业。她开了一家小型烟店并无偿地给邻居、亲友和求助者提供食宿。然而,这位“贫居窟的天使”的善心义举非但得不到好报,反而使她自己的烟店难以为继。无助的沈德只得戴上面具,以表兄水达的身份出现。“水达”待人苛刻,处事精明,他把沈德的烟店料理得井井有条。这时,从“旅途归来”的沈德爱上了一位失业飞行员。为了使他能在北京谋到职位,沈德准备卖掉烟店,大举借贷。然而她的未婚夫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骗子。他的“爱情”和沈德的善良几乎使烟店濒临倒闭。为了挽救沈德,“表兄水达”又一次登场。他在一间破屋子里开设了一家烟卷工厂,给沈德的“客人”和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残酷的剥削手段和严格的经营管理使工厂规模渐大,生意日渐兴隆。人们在感激“水达”给了他们工作和面包的同时,又十分怀念善良的沈德。于是有人怀疑“水达”谋害了他的表妹,以霸占她的烟店。“水达”被人举报。在三位神仙乔装打扮的法官面前,他现出了沈德的原形,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既要善待别人,又要善待自己,这我办不到。”“你们的世界太不公平。”然而,三个神仙在这个问题面前也束手无策。“是改变人,还是改变世界?”“是靠神仙,还是靠好人?”这就是布莱希特让观众和读者思索的问题。 对于人和世界的敏锐观察、入木三分的刻画、对于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以及驾轻就熟的大众化语言充分显示了布莱希特这位戏剧大师的手笔,这也是这个剧本获得成功、成为当代名作之一的主要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剧本里虽然出现的是中国地名和人名,然而却不一定是指中国的人和事。
保罗·策兰诗选 豆瓣
8.3 (21 个评分)
作者:
[德] 保罗·策兰
译者:
孟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9
策兰毕生以诗为生存的依托,以诗人的天性对抗历史和遗忘,创造了一种“浓缩了我们所有年期记忆”的作品。今天,许多“年期”已经被人淡忘,但在作者逝世四十年后,时间并没有磨蚀他给我们留下的诗歌遗产——我们这个既富足又贫困的时代依然缺少的一种安慰。
本书从策兰的12部诗集及遗稿里精选300多首诗歌,多篇诗作首度译成中文,并附入珍贵手稿图片及策兰夫人铜版画作。
译者弁言选摘:
以诗歌对抗历史,对抗遗忘,这使策兰的写作始终处在风暴的中心。
策兰在世时,海德格尔就已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已经远远走在了最前面,却总是自己悄悄站在最后面”。这可能是哲学家对一个诗人的最高评价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研究者,包括伽达默尔﹑波格勒﹑德里达等哲学家,阐释策兰几乎每一首诗?这并不是普通的学问兴趣。因为策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人格力量的诗人,他不仅以犀利的诗歌之刃剖开人类历史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时代出现的最暴力﹑最残酷的事件,还以他独特的语言方式创造了最优美的德语诗。
策兰没有僵硬的词语“板块”,更没有归类和贴上“意义”标签的诗歌词汇表。他只有词,两极化的词:抒情的时候,它们近得像是我们身边最日常的事物,充满亲切感;抽象的时候,意义立刻绷紧,燃烧,结晶,并且像黑色矿石那样发出光亮来。两者都提炼到它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极限。这在战后欧洲诗人的作品里是很少见的。……仿佛这里有一个泛神论的世界,起作用的是更细小的事物,矿物和诗歌元素,生活在作者赋予它们的形态和意义之中。
策兰知道卑微的事物对生活的支承力:诗,在细微之中穿过世界。
本书从策兰的12部诗集及遗稿里精选300多首诗歌,多篇诗作首度译成中文,并附入珍贵手稿图片及策兰夫人铜版画作。
译者弁言选摘:
以诗歌对抗历史,对抗遗忘,这使策兰的写作始终处在风暴的中心。
策兰在世时,海德格尔就已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已经远远走在了最前面,却总是自己悄悄站在最后面”。这可能是哲学家对一个诗人的最高评价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研究者,包括伽达默尔﹑波格勒﹑德里达等哲学家,阐释策兰几乎每一首诗?这并不是普通的学问兴趣。因为策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人格力量的诗人,他不仅以犀利的诗歌之刃剖开人类历史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时代出现的最暴力﹑最残酷的事件,还以他独特的语言方式创造了最优美的德语诗。
策兰没有僵硬的词语“板块”,更没有归类和贴上“意义”标签的诗歌词汇表。他只有词,两极化的词:抒情的时候,它们近得像是我们身边最日常的事物,充满亲切感;抽象的时候,意义立刻绷紧,燃烧,结晶,并且像黑色矿石那样发出光亮来。两者都提炼到它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极限。这在战后欧洲诗人的作品里是很少见的。……仿佛这里有一个泛神论的世界,起作用的是更细小的事物,矿物和诗歌元素,生活在作者赋予它们的形态和意义之中。
策兰知道卑微的事物对生活的支承力:诗,在细微之中穿过世界。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豆瓣
9.1 (14 个评分)
作者:
[德国] 瓦尔特·本雅明
译者:
张旭东
/
魏文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4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专著。波德莱尔对19世纪中期巴黎的现代性体验的考察深深吸引了本雅明。从这个被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异化了的抒情诗人的目光出发,本雅明希望能重新阅读处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期的巴黎。在书中,本雅明与波德莱尔一起对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渐次熄灭的煤气灯、把人固定在土地上的住房牌号、日渐堕落成商品生产者的专栏作家”发出挽歌式的哀叹,一起作为“城市的闲逛者”躲在人群里注视着这个嘈杂的商品物质世界,一起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发出“震惊”的慨叹,却又在结尾处理性而忧郁地击碎了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英雄之梦。本雅明独特的视角、细致的观察和内心的敏锐,使得这部构筑在浩瀚的引文之上的辉煌之作更多了一份诗意的绵长。
Dirty German 豆瓣
作者:
Daniel Chaffey
Ulysses Press
2009
- 4
GET D!RTY Next time you're traveling or just chattin' in German with your friends, drop the textbook formality and bust out with expressions they never teach you in school, including: Cool slang Funny insults Explicit sex terms Raw swear words Dirty German teaches the casual expressions heard every day on the streets of Germany: ♦ What's up? Wie geht's? ♦ I'm smashed. Ich bin total angeschickert. ♦ Fuckin' Munich fans. Scheiß München Fans. ♦ That shit reeks. Das riecht aber übel. ♦ I wanna shag ass. Ich will abhauen. ♦ What a complete asshole. Was für ein Arschloch. ♦ Dude, you're built like Arnold! Mensch, du bist der Arnie! About the Author Daniel Chaffey has lived in Germany for much of the last 12 years as a student, Fulbright Teaching Associate, translator and bartender, where he perfected his high German skills and learned to converse like a German sailor.
复仇女神 豆瓣
作者:
[美国] 乔纳森·利特尔
译者:
余中先
译林出版社
2010
- 8
马克西米连·奥尔,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倾心于哲学思辨,文学与音乐,期待有机会成为作家或老师。在自己理想的引导下,他选择加入纳粹党,1941年作为党卫军军官,首先随同节节胜利的德国军队来到乌克兰,在党卫军的各个先遣队里工作,参与所谓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特别行动,经历了基辅大屠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又参与了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的各项管理工作,执行对犹太人的虐待和屠杀。在柏林被苏军攻战时,奥尔杀死最好的朋友托马斯,用托马斯的证件逃出了包围圈。战后,他躲过被俘和受审,成为生产销售花边的商人,过着安逸的生活。
《复仇女神》首次从“刽子手”的内心世界出发,通过一个集体罪行参与者的记忆和讲述,探索人在杀戮之下的精神崩解。所谓的“恶”究竟是什么?国家机器是如何利用“体制”来杀人?而从最初的理想主义者变为魔鬼,人又经历了怎样内心的折磨?本书从黑暗出发,一步步走向人性中更深的黑暗。
《复仇女神》首次从“刽子手”的内心世界出发,通过一个集体罪行参与者的记忆和讲述,探索人在杀戮之下的精神崩解。所谓的“恶”究竟是什么?国家机器是如何利用“体制”来杀人?而从最初的理想主义者变为魔鬼,人又经历了怎样内心的折磨?本书从黑暗出发,一步步走向人性中更深的黑暗。
Weihnacht. Gesammelte Werke Bd. 24 豆瓣
作者:
Karl May
Karl-May-Verlag
1953
Tauben fliegen auf 豆瓣
作者:
Melinda Nadj Abonji
Jung Und Jung Verlag Gmbh
2010
- 7
Zuhause ist die Familie Kocsis in der Schweiz, doch heimisch fühlt sie sich dort nicht. Der familiäre Ursprung liegt im Norden Serbiens, dort, wo die ungarische Minderheit lebt, zu der die Kocsis auch gehören. Ausgewandert sind sie schon vor etlichen Jahren. Zuerst der Vater und dann, sobald es erlaubt war, auch die Mutter mit den beiden Töchtern, Nomi und Ildiko. Anhand einer Familie und ihrer Geheimnisse verzahnt Melinda Nadj Abonji Historisches und Privates zu einer Geschichte über die ungarische Minderheit in der Vojvodina und über den Jugoslawien-Konflikt.
城邦的世界 豆瓣
The World Of The Polis
作者: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译者:
陈周旺
译林出版社
2009
- 1
简介:
沃格林在《城邦的世界》中进行了一种“治疗性分析”。“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问题的来源,寻求秩序之道,城邦的世界之兴衰成败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导读:
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尤尔根·戈布哈特
译 后 记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埃里克·沃格林的名字是相当陌生的,远不及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卡尔·施米特这些名字那么如雷贯耳。而一旦接触沃格林的著作,更可能叫苦不迭,觉得难以卒读,遑论理解。犹记得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跟一位精研“德国流”政治哲学的美国教授聊天,讲起我正在翻译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这位美国教授连呼“Amazing”,说中国读者不可能理解沃格林,说这很可能会重蹈 “Lost in Translation”(好莱坞电影《迷失东京》的英文片名)之覆辙。他那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确实,在我接手本卷翻译之时,国内学界对于沃格林的了解即使不算空白,也是寥若晨星。此前我对沃格林的了解,也仅止于知道此君有一部名著曰《政治的新科学》。翻阅资料的结果是大失所望。那时我能拿到的关于沃格林的中文资料,仅有意大利人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一章,以及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一章中的三分之一内容(文中将沃格林的名字译为“维吉林”),另外就是西人编纂的《20世纪政治思想家辞典》中的一个条目。这样的翻译工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术语名词上,可以说都是白手起家。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近期国内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沃格林的研究性论文,以及他其中一些作品的中文译本。据我了解,也有多位学人已经,或者有意将沃格林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举凡这些,足以佐证沃格林思想的重要性,已经逐渐为国人所认识。相比之下,国外的沃格林研究要鼎盛得多了。美国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沃格林研究学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其盛况诸位从其网页上可窥见一斑;有E.桑多斯、B.库珀等当代政治哲学名家为其著书立传,编纂全集。我曾经在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看到这套摆在显眼位置的全集,心中敬意油然而生。是的,沃格林也许不属于那种“流行的”、一呼百应的思想家,但绝对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
埃里克·沃格林,1901年生于德国科隆,但他“完全是在维也纳熏陶成长起来的”,而沃格林的学术生命,严格说来,却是在美国度过和完成的。沃格林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法律,他的导师是名噪一时的法律实证主义大师凯尔森,但他似乎更关心“法国、德国哲学家以及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马斯泰罗内语),而在公众眼中,沃格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家。一切地域文化的界限,学科专业的藩篱,在沃格林身上都土崩瓦解。
写作《秩序与历史》的最初动因,乃是因为沃格林本来要写作一部《政治观念史》,无奈受限于教科书的篇幅,只好另寻出路,将这些准备好的素材独立成卷。不过,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的雄心,远远超出了“观念史”的一般化探究,而要进行一种“治疗性分析”。 “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危机的忧患意识。正所谓“乱世出真知”,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危机的来源,寻求重建和恢复秩序之道。生逢乱世,对于个人是大不幸,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沃格林还专门论证这位修昔底德与希腊医学家之间的渊源,好像故意要说明他有些像一位医生似的),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然而,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部现代性危机之下的忧愤之作呢?国人对于现代性问题已然不陌生,我们所了解的当代西方重要思想家,几乎都可以用批判现代性作为其思想的维度。沃格林当然也不例外。在他有生之年,沃格林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但与其他人不同,或者说更胜一筹的是,很多人是站在另类的立场上去批判现代性,比如诉诸古典,又或是诉诸将来,又或是诉诸超验的力量,到头来,还是各说各的话,你批判得起劲,别人照样活得潇洒。沃格林就不同了,他就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请原谅我用这个通俗的比喻),在现代性里面去反现代性,他要将现代性的烂肠烂肚全部翻出来给大家看,看它是怎样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沃格林将现代性的问题统统归结于那个著名的“诺斯替主义”或称“灵知主义”。沃格林是沿着西方思想发展的进程本身,去一路追寻现代性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这个诺斯替主义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本卷《城邦的世界》在这场追寻中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揭示了从“宇宙论神话”向“哲学”的“存在的飞跃”中,这个后来在现代世界大发神威的诺斯替主义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人的灵魂,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在宇宙论神话的秩序中,人依然仰望苍穹;但是在荷马史诗中,神的拟人化已经登峰造极;这还不算,到了赫西俄德,诗人自己走进了诗中,不再是匿名的了,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凸显出来;最后毕其功于一役的,是赫拉克利特,正是他第一个彻底地将人的灵魂发掘出来,并且让它成为灵感的源泉。可以说,政治思想史在沃格林笔下,就是一场宁静的灵魂与躁动的灵魂之间的恒久之战。
作为译者,关于沃格林我所能说的,只是个人在翻译本卷过程中一些有限的体会而已。如前所述,我对沃格林的了解几乎为零,虽然这样我有借口“悬置”一些“先天判断”,毫无障碍地直接领会沃格林的思想,但这确是一个借口而已。我实在是没有资格去评价沃格林思想的是非功过。这种捉襟见肘的介绍,无助于读者了解沃格林的思想,甚至也无助于加深对本卷的理解,因此我还是建议读者直接去阅读文本,去领会沃格林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古典素材如数家珍的深厚功力。沃格林绝非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所谓“政治哲人”,他不会用花言巧语去博取读者的追随,相反,沃格林的作品因为太“实”,太注重考据,而显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且晦涩费解。这种阅读经验,非中国读者所独有。如果本卷编者莫拉卡斯所言非虚的话,看来美国读者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兴许沃格林要告诉我们的是,政治哲学的探究,绝非逞一时之快,凭奇思妙想就可以达到,而是一次次异常艰辛的搜寻证据之旅。虽说当代政治哲学对政治学领域的科学主义潮流颇多微词,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哲学就是天马行空,不要方法,沦为意见的表达。须知在沃格林的“批判性研究”中,是没有“推论式假设”立足之地的。应该说,沃格林的作品,为我们判断政治哲学研究水准的高低优劣,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不难想见,本卷的翻译绝对是一件苦差事。而另一个让我犯难的事情就是,我对古希腊政治社会和哲学的了解,连皮毛都谈不上,每每动笔,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毫不为过。由于沃格林的作品十分诘屈聱牙,为了不败坏读者阅读的胃口,我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用比较通顺和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遮掩原作者的文风,在一些术语的表述上显得不够“专业化”,故恳请读者诸君理解我的苦心。翻译中的错误在所难免,也恳盼方家不吝批评指教,以便于本卷的修缮。
在本卷翻译过程中,我前往北京大学,与《秩序与历史》第一卷译者李强教授及其弟子叶颖博士、孔新峰博士、段保良博士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就一些术语的翻译方面达成了共识,同时也有幸直接向沃格林研究的专家尤尔根·戈布哈特教授当面请教,可谓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黄颖女士,正是在她的一再催促下我才勉力按时完成了译稿,同时她还一力承担了烦难的译稿审校工作。另外,翻译工作还得到复旦大学“金苗”项目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此刻,我不免又想起了那位美国教授的提醒。但愿《城邦的世界》的译介,不会是又一次“迷失”的开始。
陈周旺
于复旦园
沃格林在《城邦的世界》中进行了一种“治疗性分析”。“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问题的来源,寻求秩序之道,城邦的世界之兴衰成败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导读:
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尤尔根·戈布哈特
译 后 记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埃里克·沃格林的名字是相当陌生的,远不及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卡尔·施米特这些名字那么如雷贯耳。而一旦接触沃格林的著作,更可能叫苦不迭,觉得难以卒读,遑论理解。犹记得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跟一位精研“德国流”政治哲学的美国教授聊天,讲起我正在翻译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这位美国教授连呼“Amazing”,说中国读者不可能理解沃格林,说这很可能会重蹈 “Lost in Translation”(好莱坞电影《迷失东京》的英文片名)之覆辙。他那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确实,在我接手本卷翻译之时,国内学界对于沃格林的了解即使不算空白,也是寥若晨星。此前我对沃格林的了解,也仅止于知道此君有一部名著曰《政治的新科学》。翻阅资料的结果是大失所望。那时我能拿到的关于沃格林的中文资料,仅有意大利人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一章,以及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一章中的三分之一内容(文中将沃格林的名字译为“维吉林”),另外就是西人编纂的《20世纪政治思想家辞典》中的一个条目。这样的翻译工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术语名词上,可以说都是白手起家。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近期国内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沃格林的研究性论文,以及他其中一些作品的中文译本。据我了解,也有多位学人已经,或者有意将沃格林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举凡这些,足以佐证沃格林思想的重要性,已经逐渐为国人所认识。相比之下,国外的沃格林研究要鼎盛得多了。美国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沃格林研究学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其盛况诸位从其网页上可窥见一斑;有E.桑多斯、B.库珀等当代政治哲学名家为其著书立传,编纂全集。我曾经在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看到这套摆在显眼位置的全集,心中敬意油然而生。是的,沃格林也许不属于那种“流行的”、一呼百应的思想家,但绝对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
埃里克·沃格林,1901年生于德国科隆,但他“完全是在维也纳熏陶成长起来的”,而沃格林的学术生命,严格说来,却是在美国度过和完成的。沃格林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法律,他的导师是名噪一时的法律实证主义大师凯尔森,但他似乎更关心“法国、德国哲学家以及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马斯泰罗内语),而在公众眼中,沃格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家。一切地域文化的界限,学科专业的藩篱,在沃格林身上都土崩瓦解。
写作《秩序与历史》的最初动因,乃是因为沃格林本来要写作一部《政治观念史》,无奈受限于教科书的篇幅,只好另寻出路,将这些准备好的素材独立成卷。不过,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的雄心,远远超出了“观念史”的一般化探究,而要进行一种“治疗性分析”。 “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危机的忧患意识。正所谓“乱世出真知”,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危机的来源,寻求重建和恢复秩序之道。生逢乱世,对于个人是大不幸,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沃格林还专门论证这位修昔底德与希腊医学家之间的渊源,好像故意要说明他有些像一位医生似的),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然而,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部现代性危机之下的忧愤之作呢?国人对于现代性问题已然不陌生,我们所了解的当代西方重要思想家,几乎都可以用批判现代性作为其思想的维度。沃格林当然也不例外。在他有生之年,沃格林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但与其他人不同,或者说更胜一筹的是,很多人是站在另类的立场上去批判现代性,比如诉诸古典,又或是诉诸将来,又或是诉诸超验的力量,到头来,还是各说各的话,你批判得起劲,别人照样活得潇洒。沃格林就不同了,他就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请原谅我用这个通俗的比喻),在现代性里面去反现代性,他要将现代性的烂肠烂肚全部翻出来给大家看,看它是怎样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沃格林将现代性的问题统统归结于那个著名的“诺斯替主义”或称“灵知主义”。沃格林是沿着西方思想发展的进程本身,去一路追寻现代性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这个诺斯替主义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本卷《城邦的世界》在这场追寻中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揭示了从“宇宙论神话”向“哲学”的“存在的飞跃”中,这个后来在现代世界大发神威的诺斯替主义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人的灵魂,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在宇宙论神话的秩序中,人依然仰望苍穹;但是在荷马史诗中,神的拟人化已经登峰造极;这还不算,到了赫西俄德,诗人自己走进了诗中,不再是匿名的了,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凸显出来;最后毕其功于一役的,是赫拉克利特,正是他第一个彻底地将人的灵魂发掘出来,并且让它成为灵感的源泉。可以说,政治思想史在沃格林笔下,就是一场宁静的灵魂与躁动的灵魂之间的恒久之战。
作为译者,关于沃格林我所能说的,只是个人在翻译本卷过程中一些有限的体会而已。如前所述,我对沃格林的了解几乎为零,虽然这样我有借口“悬置”一些“先天判断”,毫无障碍地直接领会沃格林的思想,但这确是一个借口而已。我实在是没有资格去评价沃格林思想的是非功过。这种捉襟见肘的介绍,无助于读者了解沃格林的思想,甚至也无助于加深对本卷的理解,因此我还是建议读者直接去阅读文本,去领会沃格林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古典素材如数家珍的深厚功力。沃格林绝非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所谓“政治哲人”,他不会用花言巧语去博取读者的追随,相反,沃格林的作品因为太“实”,太注重考据,而显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且晦涩费解。这种阅读经验,非中国读者所独有。如果本卷编者莫拉卡斯所言非虚的话,看来美国读者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兴许沃格林要告诉我们的是,政治哲学的探究,绝非逞一时之快,凭奇思妙想就可以达到,而是一次次异常艰辛的搜寻证据之旅。虽说当代政治哲学对政治学领域的科学主义潮流颇多微词,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哲学就是天马行空,不要方法,沦为意见的表达。须知在沃格林的“批判性研究”中,是没有“推论式假设”立足之地的。应该说,沃格林的作品,为我们判断政治哲学研究水准的高低优劣,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不难想见,本卷的翻译绝对是一件苦差事。而另一个让我犯难的事情就是,我对古希腊政治社会和哲学的了解,连皮毛都谈不上,每每动笔,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毫不为过。由于沃格林的作品十分诘屈聱牙,为了不败坏读者阅读的胃口,我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用比较通顺和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遮掩原作者的文风,在一些术语的表述上显得不够“专业化”,故恳请读者诸君理解我的苦心。翻译中的错误在所难免,也恳盼方家不吝批评指教,以便于本卷的修缮。
在本卷翻译过程中,我前往北京大学,与《秩序与历史》第一卷译者李强教授及其弟子叶颖博士、孔新峰博士、段保良博士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就一些术语的翻译方面达成了共识,同时也有幸直接向沃格林研究的专家尤尔根·戈布哈特教授当面请教,可谓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黄颖女士,正是在她的一再催促下我才勉力按时完成了译稿,同时她还一力承担了烦难的译稿审校工作。另外,翻译工作还得到复旦大学“金苗”项目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此刻,我不免又想起了那位美国教授的提醒。但愿《城邦的世界》的译介,不会是又一次“迷失”的开始。
陈周旺
于复旦园
少年维特的烦恼 豆瓣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8.5 (54 个评分)
作者:
[德]歌德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译者:
侯浚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8
歌德(1749一1832),德国文豪。《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他早年最重要的作品。 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作者创作它时年仅二十五岁。小说描写进步青年对当时鄙陋的德国社会的体验和感受,表现了作者对封建道德等级观念的反应以及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少年维特爱上了一个名叫绿蒂的姑娘,而姑娘已同别人订婚。爱情上的挫折使维特悲痛欲绝。之后,维特又因同封建社会格格不入,感到前途无望而自杀。 《少年维特的烦恼》于一七七五年问世,它的出版被认为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曾震撼了德国乃至欧洲整整一代青年的心。
Die Welt ist groß und Rettung lauert überall. 豆瓣
作者:
Ilija Trojanow
Dtv
1999
- 7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Sonderausgabe. Zwei Bände im Schuber. 豆瓣
作者: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Beck C. H.
2002
- 8
德国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德国直到19世纪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比英国和法国都要晚。直到1806年,才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它其实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复杂的实体,一个旧式的、古老的政治体。将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语言,语言在19世纪对德国认同感的作用是非常独特的。直到1871年俾斯麦武装了德意志帝国以后,德国人才获得了认同感的政治框架。俾斯麦帝国还发展起某种政治上的认同。但在俾斯麦界定的政治上的德国和文化上的德国之间仍有区别,后者还包括奥地利,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和瑞士讲德语的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他们的政治哲学视为反西方的。1918年,托马斯·曼初版了《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他在书中将西方文明和德国文化对立起来。当1918年、1919年西方民主制度终于被引入魏玛共和国的时候,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体系,是胜利者强加给德国人的。“胜利者的制度”这一称谓,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利用来激发反西方的情绪。对西方的反感终于在二战后被克服了,对西方价值政治上的采纳开始于前联邦德国。1986年,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做了一个概括,我经常引用它,因为非常精彩。哈贝马斯写道:“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无条件开放,是战后时代智识上的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引以为豪的。”1990年,德国问题终于经由统一而得到解决,整个德国进入了西方民主制度。德国问题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一直存在,它是自由和统一的问题,也是个疆界的问题。疆界问题在1990年德国和波兰确认边界后解决了,自由和统一问题在1990年10月因东德接受德国宪法而获解决。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豆瓣
作者: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C.H.Beck
2005
- 7
Hitlers Volksstaat 豆瓣
作者:
Götz Aly
Fischer (S.), Frankfurt
2005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