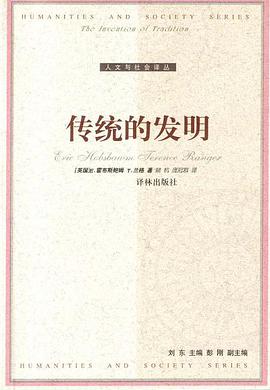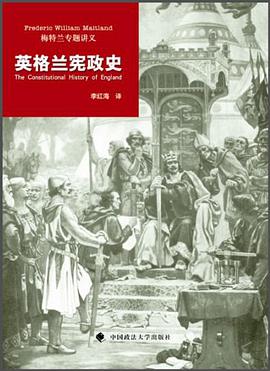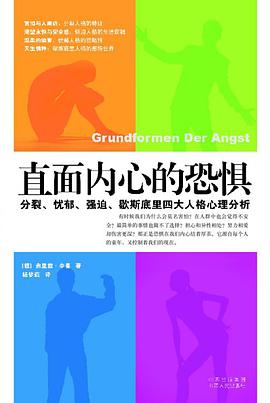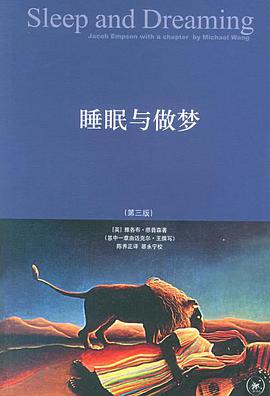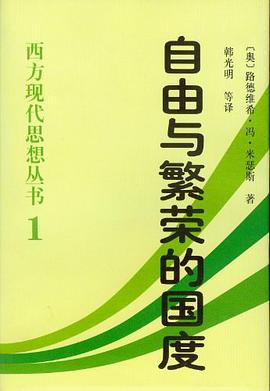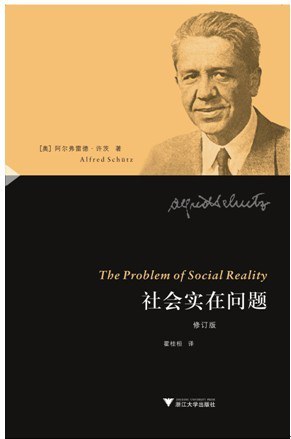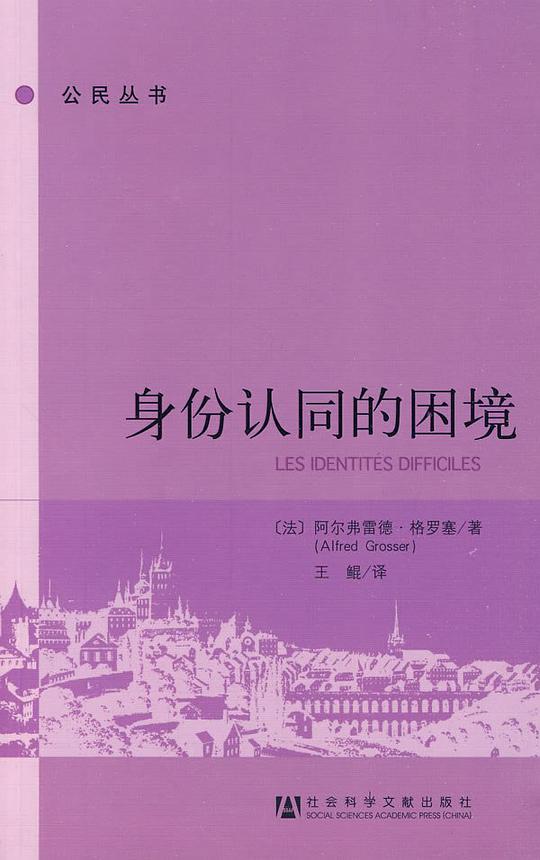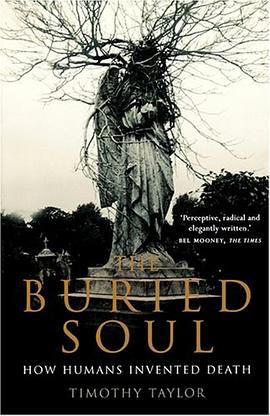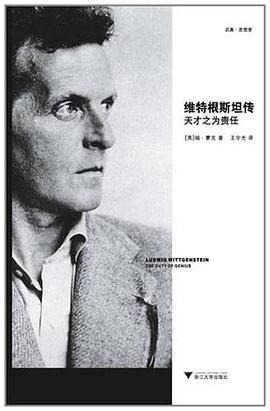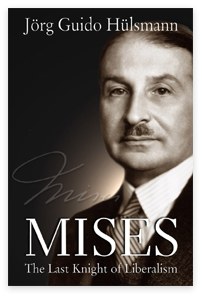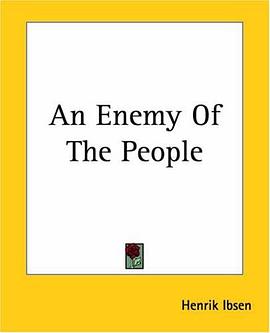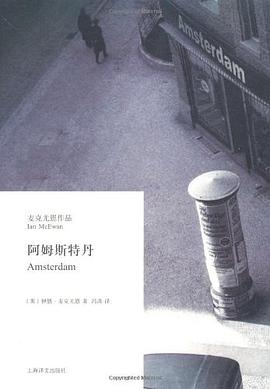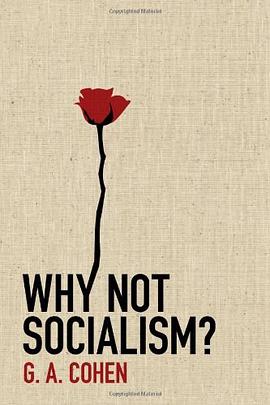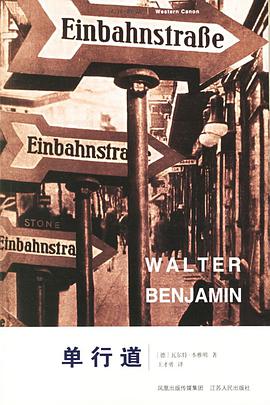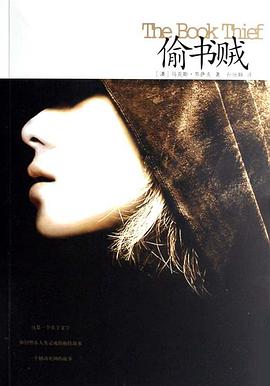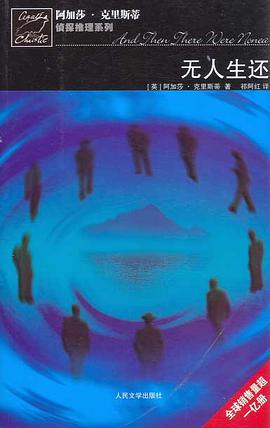歐洲
传统的发明 豆瓣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8.5 (8 个评分)
作者:
(英国)E.霍布斯鲍姆//T.兰格
译者:
顾杭
/
庞冠群
译林出版社
2004
- 3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英格兰宪政史 豆瓣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作者:
[英] F. W. 梅特兰
译者:
李红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这是剑桥大学梅特兰教授向学生讲授英格兰宪政史的课堂讲义的译著。原著作者将英格兰公法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立法的总体特征、王权、议会、中央及地方政府、司法等方面的宪政运作状况予以了总结介绍,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晰完美地梳理了英格兰法律发展和宪政运作脉络。本书虽非梅特兰精雕细琢之成熟作品,但并非简单的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是着眼于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审视和探讨,背景资料翔实,分析细致入微并涵盖了大量的原创性观点,为我们学习和研究英格兰宪政史提供了很好的引领。其独特的阶段划分方法也为我们研究英国宪政史提供了不同寻常的观测点,对既有历史著述做出了重要补充。本书系统全面,条理清晰,翻译流畅,完全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广大比较法研究者、法学研究者以及法学爱好者、英国宪政史、法律发展史研究者以及英国政治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
直面内心的恐惧 豆瓣
7.8 (16 个评分)
作者:
[德] 弗里兹·李曼
译者:
杨梦茹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10
如果你是心理学的门外汉,对心理学一窍不通,却想认识人类性格的差异,那么《直面内心的恐惧:分裂、忧郁、强迫、歇斯底里四大人格心理分析》所概括的内容和易于理解的叙述方式,是一本值得推荐的“性格心理学”入门书。
作者弗里兹•李曼以地球的行星运转原理——自转、公转、向心力和离心力为模式,分类出四种恐惧的原型:害怕把自己交出去、害怕做自己、害怕改变以及害怕既定的规律。由这四种恐惧原型为出发点,书中分类出四种与之对等的人格类型——精神分裂、忧郁、强迫和歇斯底里人格。每一章都以理论为开端,从情感、侵略性、环境的角度,并辅以他行医多年搜集到的真实故事,微视每种人格的心理冲突、运作机制,及其行为表征。进而深入患者自幼及成长的环境因素,用重新建构的方式,恢复支离破碎的原始经验,给患者以治疗。
这本书是为每一个人而写的,目的在于帮助大家多了解自己与他人,有助于探索自身恐惧的来源,抚慰我们受伤的身心,并在四种恐惧之间取得健康的平衡点。
作者弗里兹•李曼以地球的行星运转原理——自转、公转、向心力和离心力为模式,分类出四种恐惧的原型:害怕把自己交出去、害怕做自己、害怕改变以及害怕既定的规律。由这四种恐惧原型为出发点,书中分类出四种与之对等的人格类型——精神分裂、忧郁、强迫和歇斯底里人格。每一章都以理论为开端,从情感、侵略性、环境的角度,并辅以他行医多年搜集到的真实故事,微视每种人格的心理冲突、运作机制,及其行为表征。进而深入患者自幼及成长的环境因素,用重新建构的方式,恢复支离破碎的原始经验,给患者以治疗。
这本书是为每一个人而写的,目的在于帮助大家多了解自己与他人,有助于探索自身恐惧的来源,抚慰我们受伤的身心,并在四种恐惧之间取得健康的平衡点。
睡眠与做梦 豆瓣
Sleep and Dreaming
作者:
[英] 雅各布·恩普森
译者:
陈养正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昼夜的划分,必定是地球生活中最深奥的奇事之一。总而言之,它是一种仁厚的安排,既令我们得以借助自己设定的短暂木憩来恢复活力,免于劳顿而无法自拔,也不至于因为时光的不断飞逝而受到责难。我们是间歇性的生物,总是黎明即起、日落欢息。我们的意识会很快疲劳,因此要间歇地运作,而翌日的世界将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或者令我们舒服,或者令我们不安;同样地,夜晚与睡眠相伴随,以甜蜜的影像巧妙地满足我们之所需。这一切令人类惊叹不已。生物时常不知不觉地进阙如少觉的暗黑梦乡,去体验大量的幻象,连天使都为之惊叹。我们的主命如此之脆弱,却能够经受这样不同的极端,从来不曾有任何哲学家对此给出过解释。 ——艾丽斯·默多克《黑王子》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豆瓣
A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9.0 (8 个评分)
作者:
[奥地利]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译者:
韩光明 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1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许多人观念中的自由主义其实仅仅局限于它作为政治思潮的方面。其实,自由主义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制度的社会思潮。本书详尽的介绍了自由主义的特征,它的政策的基础、它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自由主义与政党、自由主义的前途诸多方面。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比较博大的观念,它表示一种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选择生产资料私有制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生前曾长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是米瑟斯于1927年发表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原名是《自由主义》,1962年在美国出版英译本,名为《自由与成功的共同富裕》。中译本是我们根据1927年德国耶拿出版社的德文版翻译而成的。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生前曾长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是米瑟斯于1927年发表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原名是《自由主义》,1962年在美国出版英译本,名为《自由与成功的共同富裕》。中译本是我们根据1927年德国耶拿出版社的德文版翻译而成的。
知识分子的鸦片 豆瓣 Goodreads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7.6 (10 个评分)
作者:
(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译者:
吕一民
/
顾杭
译林出版社
2005
- 7
简介: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导读: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导读: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社会静力学 豆瓣
作者:
赫伯特﹒斯宾塞
译者:
张雄武
商务印书馆
1996
- 11
序
这部著作于1850年12月出版时,按其原来形式,名为《社会静力学:或,人类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经过了好几年——我想大约10年——这一版售罄,因为需求似乎不太大,没有理由重排新版,决定由美国进口一版——当时在美国,本书已用铅版印刷。在这一版售出后,第三版也是同样进口的。
这时我已摒弃由原来制定的第一原理引出的某些结论。此外,虽然我仍旧信奉这项第一原理,但作为提出它的根据之一也已被我放弃。因此在接连几版前面我都附加声明,表示某些原来宣布的理论需要修改;但我却没有做这些需要做的改动,因为如果做这些改动,我就不得不搁置更加重要的工作。终于,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我的预先声明没有阻止别人对我后来的信仰产生误解;因此,10年前,在第三版书全部售完后,我决定不再用进口来满足仍然存在的需求。
可是,既然已经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许多推论仍然存留在我心里,我就一直想把它们用一种永久性的容易查找的形式保存下来;于是在1890年,我在暇时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一遍,删去某些部分,压缩另一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文字上的修订。其完全自成体系的部分现在被《伦理学原理:公正》一书的第四部分代替了;在这一部分里原来以不完善形式阐述的伦理学说,不再那么粗糙,而成为科学的有连贯性的了。但是《公正》一书既没有包括《社会静力学》一书内建设性部分之前的讨论,也没有包括在快结尾时指出政治上含义的一系列章节;而这两部分似乎都是值得保留的。
我也希望保留某些段落。它们包含了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一些思想或思想的萌芽。这些段落具有一种传记—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见第27—28页、30—32页、117—118页、143—144页、173页、196—198页、235—236页、240—243页、257—260页。
这部著作的后一部分,多处引述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和写作时还存在的机构;由于随后40年中社会的变化,它们已不那么切题,或者变得毫不相干了。但是似乎最好还是让它们照原样保留下来;这部分是因为虽然它们根据的资料已经改变,那些论证却仍然有效;部分是因为如果代之以别的例证,就需要我付出比目前我能付出的更多劳动;部分是因为即使把例证改为切合当今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很快又会变成陈旧的。
我最初想把这本书,或更确切地说,一本书的一部分,称为《社会静力学片断》,后来又想称为《社会静力学选编》。可是这两个书名所表示的似乎都是若干部分的集合体,远未反映它实际所包含的连贯性。另一方面,称之为节略本也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词不能表明若干大的、结构上重要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没有一个书名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最后我判定还是《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这个书名不恰当的程度最小。
1892年1月于伦敦
这部著作于1850年12月出版时,按其原来形式,名为《社会静力学:或,人类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经过了好几年——我想大约10年——这一版售罄,因为需求似乎不太大,没有理由重排新版,决定由美国进口一版——当时在美国,本书已用铅版印刷。在这一版售出后,第三版也是同样进口的。
这时我已摒弃由原来制定的第一原理引出的某些结论。此外,虽然我仍旧信奉这项第一原理,但作为提出它的根据之一也已被我放弃。因此在接连几版前面我都附加声明,表示某些原来宣布的理论需要修改;但我却没有做这些需要做的改动,因为如果做这些改动,我就不得不搁置更加重要的工作。终于,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我的预先声明没有阻止别人对我后来的信仰产生误解;因此,10年前,在第三版书全部售完后,我决定不再用进口来满足仍然存在的需求。
可是,既然已经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许多推论仍然存留在我心里,我就一直想把它们用一种永久性的容易查找的形式保存下来;于是在1890年,我在暇时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一遍,删去某些部分,压缩另一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文字上的修订。其完全自成体系的部分现在被《伦理学原理:公正》一书的第四部分代替了;在这一部分里原来以不完善形式阐述的伦理学说,不再那么粗糙,而成为科学的有连贯性的了。但是《公正》一书既没有包括《社会静力学》一书内建设性部分之前的讨论,也没有包括在快结尾时指出政治上含义的一系列章节;而这两部分似乎都是值得保留的。
我也希望保留某些段落。它们包含了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一些思想或思想的萌芽。这些段落具有一种传记—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见第27—28页、30—32页、117—118页、143—144页、173页、196—198页、235—236页、240—243页、257—260页。
这部著作的后一部分,多处引述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和写作时还存在的机构;由于随后40年中社会的变化,它们已不那么切题,或者变得毫不相干了。但是似乎最好还是让它们照原样保留下来;这部分是因为虽然它们根据的资料已经改变,那些论证却仍然有效;部分是因为如果代之以别的例证,就需要我付出比目前我能付出的更多劳动;部分是因为即使把例证改为切合当今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很快又会变成陈旧的。
我最初想把这本书,或更确切地说,一本书的一部分,称为《社会静力学片断》,后来又想称为《社会静力学选编》。可是这两个书名所表示的似乎都是若干部分的集合体,远未反映它实际所包含的连贯性。另一方面,称之为节略本也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词不能表明若干大的、结构上重要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没有一个书名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最后我判定还是《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这个书名不恰当的程度最小。
1892年1月于伦敦
身份认同的困境 豆瓣
作者:
(法) 格罗塞
译者:
王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2
《身份认同的困境》内容简介:我是何人?我们又是谁?谁来定义“我们”呢?我们认定“他们”是什么人?界定“他们”的基础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无论是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还是在跨国空间内。在此意义上,“欧洲”这个不明确的概念构成了一个绝好的身份认同之因素相互交织的例子。
经历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这些传递的影响铸就了各种身份。身份概念影响到人类群体构思和组织其未来的方式,即对政治事务的组织。在当前身份问题日渐凸显之际,对此进行思考显得尤为可贵。
随着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移民潮的发展,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困扰社会、国家、民族、社群和个人,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身份认同的困境》基于欧洲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而出现的种种疑惑,从政治身份、个人身份、集体身份、欧洲身份及价值观身份等方面来探讨身份的多样性和认同的变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趋势,加深对欧美社会和舆情的了解。
经历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这些传递的影响铸就了各种身份。身份概念影响到人类群体构思和组织其未来的方式,即对政治事务的组织。在当前身份问题日渐凸显之际,对此进行思考显得尤为可贵。
随着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移民潮的发展,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困扰社会、国家、民族、社群和个人,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身份认同的困境》基于欧洲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而出现的种种疑惑,从政治身份、个人身份、集体身份、欧洲身份及价值观身份等方面来探讨身份的多样性和认同的变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趋势,加深对欧美社会和舆情的了解。
The Buried Soul 豆瓣
作者:
Taylor, Timothy
Beacon
2008
- 7
Taylor's entertaining, if grisly, interpretative history turns the raw gleanings of two centuries of archaeology on their head. Referencing his own experience, as well as others' documented discoveries, he expounds on the pervasiveness of such practices as funerary cannibalism, vampirism, and human sacrifice, and he poses the question, Which came first, the notion of the soul or the ceremonial burial of remains?
His conclusions, as he acknowledges, may be somewhat unsettling. Caches of bones, pottery shards, and tools reveal only the most basic clues, and the majority of archaeologists, filtering those clues through their modern "visceral insulation" from things pertaining to death, are, by Taylor's lights, unable to acknowledge how prevalent cannibalism and ritual sacrifice were and are.
Furthermore, while widespread popular thought maintains that humans acquired belief in the soul first and then developed ritual burial, Taylor considers the reverse to be more accurate: the immortal soul was invented as a result of the first burial ceremonies. Taylor demonstrates, albeit in highly scholarly style, the value of postulating well-developed, opposing points of view. (by Donna Chavez)
His conclusions, as he acknowledges, may be somewhat unsettling. Caches of bones, pottery shards, and tools reveal only the most basic clues, and the majority of archaeologists, filtering those clues through their modern "visceral insulation" from things pertaining to death, are, by Taylor's lights, unable to acknowledge how prevalent cannibalism and ritual sacrifice were and are.
Furthermore, while widespread popular thought maintains that humans acquired belief in the soul first and then developed ritual burial, Taylor considers the reverse to be more accurate: the immortal soul was invented as a result of the first burial ceremonies. Taylor demonstrates, albeit in highly scholarly style, the value of postulating well-developed, opposing points of view. (by Donna Chavez)
An Enemy Of The People 豆瓣
作者:
Ibsen, Henrik
2004
- 6
Hovstad. I am of humble origin, as you know; and that has given me opportunities of knowing what is the most crying need in the humbler ranks of life. It is that they should be allowed some part in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affairs, Doctor. That is what will develop their faculties and intelligence and self respect.
阿姆斯特丹 豆瓣
Amsterdam
7.5 (16 个评分)
作者:
[英国] 伊恩·麦克尤恩
译者:
冯涛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7
《阿姆斯特丹》是一部无比精妙的作品。故事围绕两个好朋友——克莱夫和弗农展开:克莱夫是有名的作曲家,弗农是报社主编——在前情人的葬礼上,两人相遇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个主人公曾经共同拥有过这个死去的女人。这个死去的漂亮、浑身散发着魅力的女人是饭店批评家、摄影师莫莉。两人无法想象莫莉竟然与保守的外交大臣加莫尼有瓜葛,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嫁给庸俗但富有的乔治。他们对莫莉死前遭受的痛苦深感痛惜,于是他们达成协议:如果对方不能有尊严的活下去时,对方可以随时结束他的生命。
紧接着,克莱夫和弗农都陷入到一场意外的危机之中:克莱夫必须完成他的《千禧年交响乐》,只有这样才能在阿姆斯特丹进行首次公演;弗农必须在是否刊登加莫尼的变态照片问题上作出抉择。纯洁的艺术重要还是政治责任或者是经济偿付能力重要,在这三者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所有的一切使弗农和克莱夫反目为仇,彼此都想以同样的方式至对方于死地,以泄心头之恨。而更多意料之外的谣言与传闻他们更加不知所措,所有的一切都因何而来,究竟是真是假?
邪恶、欺骗、背叛、罪孽、谋杀、奸诈……人性的种种在此淋漓尽致地展开。
紧接着,克莱夫和弗农都陷入到一场意外的危机之中:克莱夫必须完成他的《千禧年交响乐》,只有这样才能在阿姆斯特丹进行首次公演;弗农必须在是否刊登加莫尼的变态照片问题上作出抉择。纯洁的艺术重要还是政治责任或者是经济偿付能力重要,在这三者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所有的一切使弗农和克莱夫反目为仇,彼此都想以同样的方式至对方于死地,以泄心头之恨。而更多意料之外的谣言与传闻他们更加不知所措,所有的一切都因何而来,究竟是真是假?
邪恶、欺骗、背叛、罪孽、谋杀、奸诈……人性的种种在此淋漓尽致地展开。
Why Not Socialism? 豆瓣
作者:
G. A. Coh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8
Is socialism desirable? Is it even possible? In this concise book,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presents with clarity and wit a compelling moral case for socialism and argues that the obstacles in its way are exaggerated. There are times, G. A. Cohen notes, when we all behave like socialists. On a camping trip, for example, campers wouldn't dream of charging each other to use a soccer ball or for fish that they happened to catch. Campers do not give merely to get, but relate to each other in a spirit of equality and community. Would such socialist norms be desirable across society as a whole? Why not? Whole societies may differ from camping trips, but it is still attractive when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with the equal regard that such trips exhibit. But, however desirable it may be, many claim that socialism is impossible. Cohen writes that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socialism isn't, as often argued, intractable human selfishness - it's rather the lack of obvious means to harness the human generosity that is there. Lacking those means, we rely on the market. But there are many ways of confining the sway of the market: there are desirable changes that can move us toward a socialist society in which, to quote Albert Einstein, humanity has 'overcome and advanced beyond the predatory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单行道 Eggplant.place 豆瓣
6.4 (32 个评分)
作者:
[德国] 瓦尔特·本雅明
译者:
王才勇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3
这本书是本雅明的名作之一,一部意象集。这些意象都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中的真实事物,比如邮票、加油站、早餐室、中国古董、手套、时钟,建筑工地、海报、啤酒馆等等,当然还有梦境。本雅明对这些事物的处理不是找一堆概念来辅佐,而是直接从事物本身深挖下去,找出文化深处与人的感性、理性深处的暗流。本雅明所观注的这些事物已随着时间而逝,但是本雅明的思想却仍然新鲜,对当今世界的学术、思想界依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偷书贼 豆瓣
The Book Thief
8.1 (121 个评分)
作者:
[澳] 马克斯·苏萨克
译者:
孙张静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 8
1939年的德国,9岁的小女孩莉赛尔和弟弟被迫送往慕尼黑远郊的寄养家庭。6岁的弟弟不幸死在了路途中。在冷清的葬礼后,莉赛尔意外得到她的第一本书《掘墓人手册》。
这将是14本给她带来无限安慰的书之一。她是个孤苦的孩子,父亲被打上了共产主义者的烙印,被纳粹带走了;母亲随后也失踪了。在弹奏手风琴的养父的帮助下,她学会了阅读。尽管生活艰苦,她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她忍不住开始偷书。莉赛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
这是个讲述书是如何振奋灵魂的令人难忘的故事。
这将是14本给她带来无限安慰的书之一。她是个孤苦的孩子,父亲被打上了共产主义者的烙印,被纳粹带走了;母亲随后也失踪了。在弹奏手风琴的养父的帮助下,她学会了阅读。尽管生活艰苦,她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她忍不住开始偷书。莉赛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
这是个讲述书是如何振奋灵魂的令人难忘的故事。
无人生还 豆瓣 Media of OOIS Goodreads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8.9 (389 个评分)
作者: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者:
祁阿红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 3
十个互不相识的人,被富有的欧文先生邀请到了印地安岛上的私人别墅里。晚餐后,一个神秘的声音揭开了人们心中所各自隐藏着的可怕秘密。当天晚上,年轻的马斯顿先生离奇死去,古老的童谣就像诅咒一样笼罩着所有人,似乎有一双神秘的眼镜在时刻窥视着这场死亡游戏,到访者就像消失的印地安小瓷人一样一个又一个的走向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