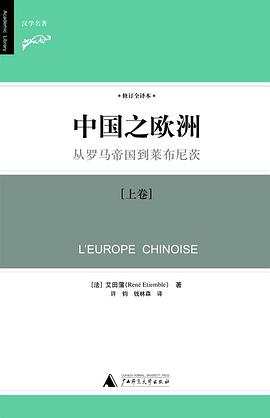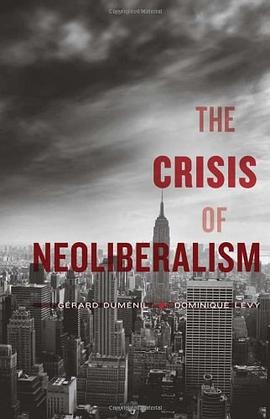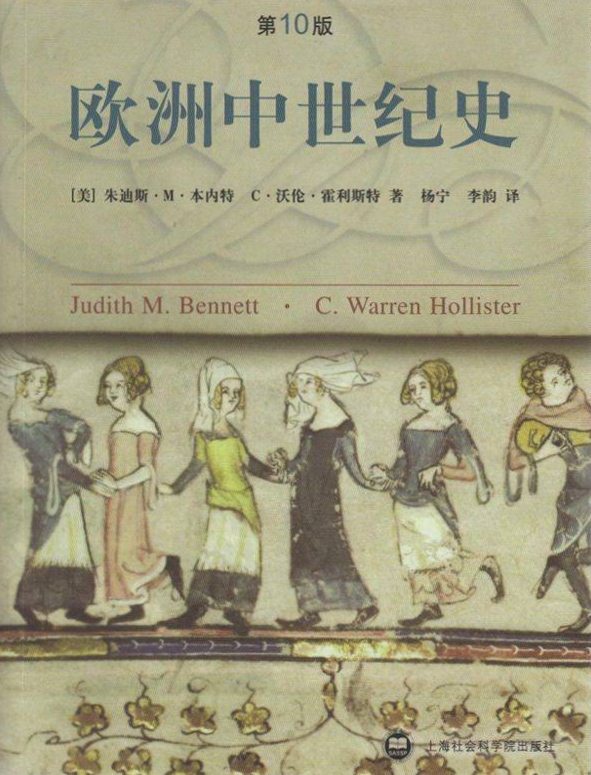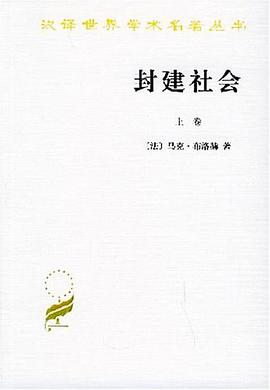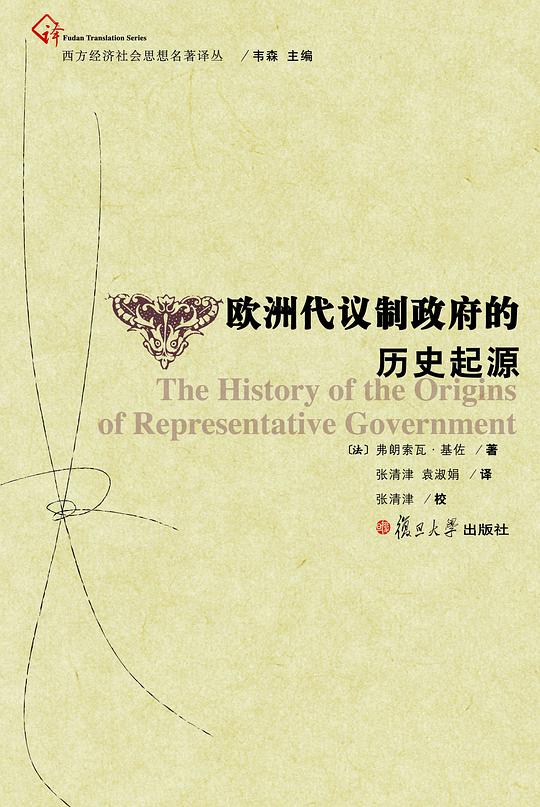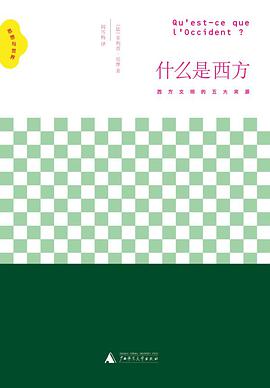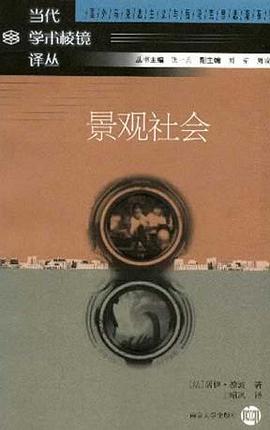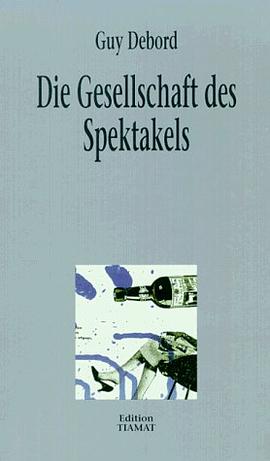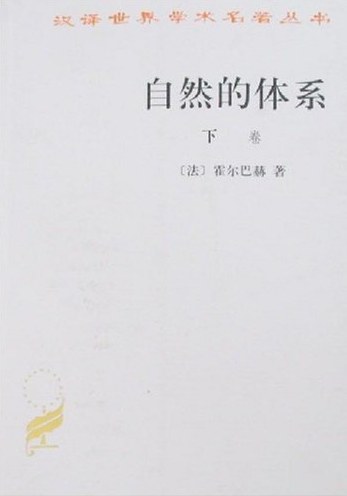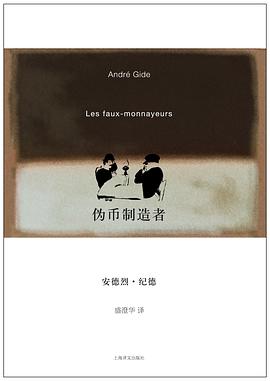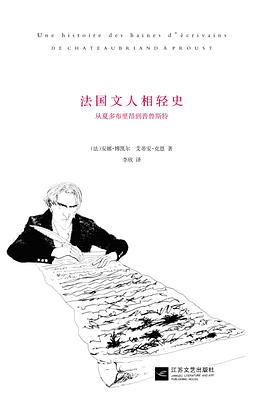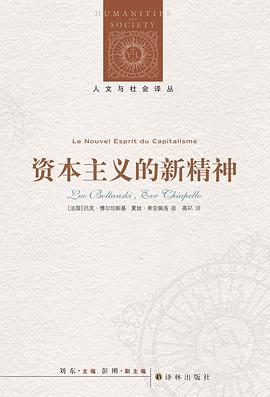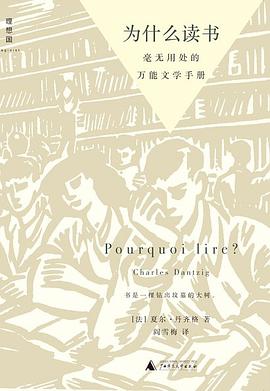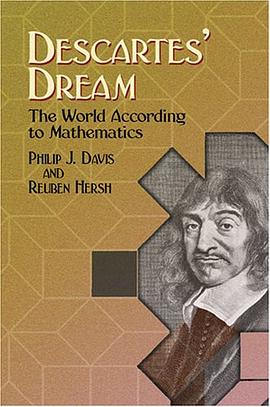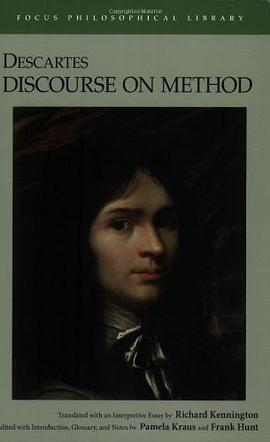中国之欧洲(修订译本) 豆瓣
作者:
艾田蒲
译者:
许钧
/
钱林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8
《中国之欧洲》是饮誉世界的汉学家、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教授几十年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一部比较文化力作。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开阔的东方意识,从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对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作了十分精当的描述和独到的研究,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欧洲中心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西方学术史和比较文学发展史来考虑, 《中国之欧洲》是20世纪比较文学和西方汉学牵手、搭桥的先驱之作,艾田蒲顺应近代西方学术潮流,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贡献了这部跨文化、多学科联姻和对话的典型范本。如今,这部大着已经走进中国大学课堂,是无数专攻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化关系的年轻学子必读的经典著作。
上卷目录摘要
追忆艾田蒲(代修订译本序)
中文版序
法文版序
前言
第一部 契丹寻踪
第一章 契丹寻踪
第二章 耶稣会传教团之前在中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1)
第四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2)
第五章 从阿拉伯人的游记到马可•波罗纪行
第六章 马可•波罗(1)
第七章 马可•波罗(2)
第八章 马可•波罗(3)
第九章 中国艺术与锡耶纳复兴
第十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和地狱表现的影响
第十一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1)
第十二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2)
……
下卷目录摘要
前言
第一部 罗马教廷否认耶稣会士眼中的中国之欧洲
第一章 图尔侬事件结局不妙
第二章 梅扎巴尔巴在中国与伏尔泰的缄默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
第四章 欧洲仍在中国化
第五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1)
第六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2)
第二部 17和18世纪欧洲戏剧中的几个中国侧面
第七章 伊丽莎白戏剧
第八章 司马迁的《中国孤儿》
第九章 纪君祥的《中国孤儿》
第十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
第十一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第十二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
……
译后记
人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书刊名中外文对照表
从西方学术史和比较文学发展史来考虑, 《中国之欧洲》是20世纪比较文学和西方汉学牵手、搭桥的先驱之作,艾田蒲顺应近代西方学术潮流,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贡献了这部跨文化、多学科联姻和对话的典型范本。如今,这部大着已经走进中国大学课堂,是无数专攻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化关系的年轻学子必读的经典著作。
上卷目录摘要
追忆艾田蒲(代修订译本序)
中文版序
法文版序
前言
第一部 契丹寻踪
第一章 契丹寻踪
第二章 耶稣会传教团之前在中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1)
第四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2)
第五章 从阿拉伯人的游记到马可•波罗纪行
第六章 马可•波罗(1)
第七章 马可•波罗(2)
第八章 马可•波罗(3)
第九章 中国艺术与锡耶纳复兴
第十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和地狱表现的影响
第十一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1)
第十二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2)
……
下卷目录摘要
前言
第一部 罗马教廷否认耶稣会士眼中的中国之欧洲
第一章 图尔侬事件结局不妙
第二章 梅扎巴尔巴在中国与伏尔泰的缄默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
第四章 欧洲仍在中国化
第五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1)
第六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2)
第二部 17和18世纪欧洲戏剧中的几个中国侧面
第七章 伊丽莎白戏剧
第八章 司马迁的《中国孤儿》
第九章 纪君祥的《中国孤儿》
第十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
第十一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第十二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
……
译后记
人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书刊名中外文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