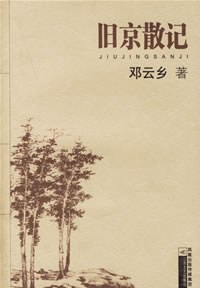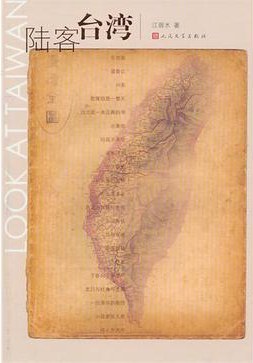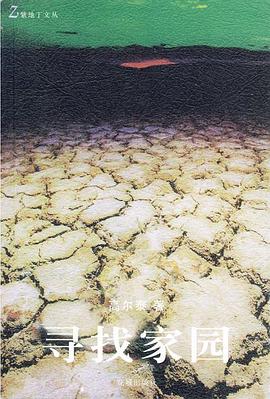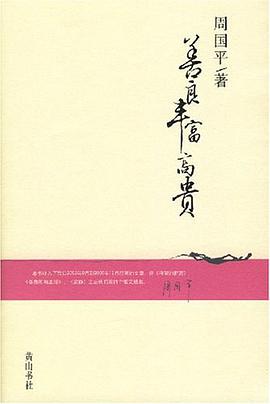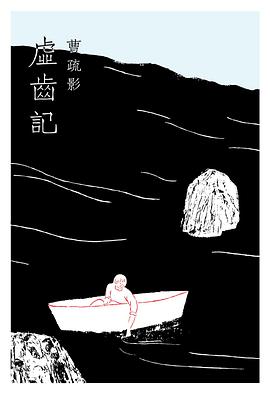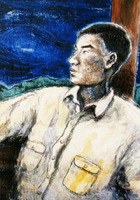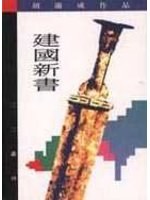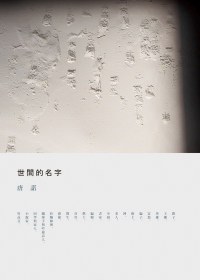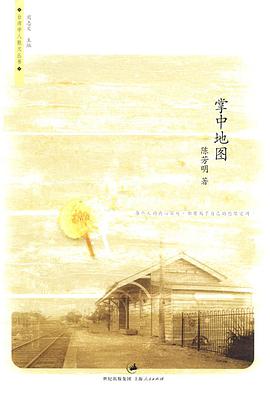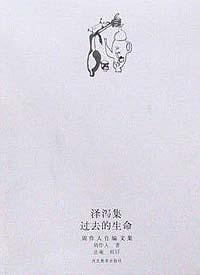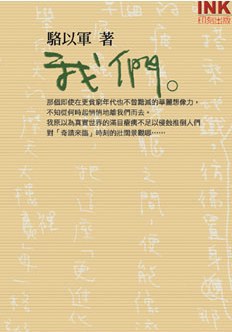散文
善良丰富高贵 豆瓣
7.0 (6 个评分)
作者:
周国平
黄山书社
2007
- 7
如果我是一个从前的哲人,来到今天的世界,我会最怀念什么?一定是这六个字:善良,丰富,高贵。我听见一切世代的哲人在向今天的人们呼唤:人啊,你要有善良的心,丰富的心灵,高贵的灵魂,这样你才无愧于人的称号,你才是作为真正的人在世间生活。善良、丰富、高贵——令人怀念的品质,人之为人的品质,我期待今天更多的人拥有它们。本书收入了我自2002年8月至2006年12月所写的文章,是《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之后的第四个散文结集。我一向不高产,前三次结集,间隔是三年上下,这次超过了四年。四年多的文字往这里一堆,内容显得芜杂,我自己看了也惭愧。这四年多里,含我的一个本命年,而且是岁满甲子的大本命年。有一天,我去单位,人事干部把一个崭新的退休证交给我,没有让我填任何表格、办任何手续,我欣赏这不同寻常的效率。我也欣赏我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他知道我的脾气,免去了例行的嗑瓜子、讲客套话的告别会。总之,我清清爽爽地退休了。常有人不平,说我这样的学者,精力正旺盛,不该这么早让退休。他们真是不了解国情。其实,在现行体制下,如我之辈,对学术机构里的官场规则、潜规则不感兴趣也一窍不通,单位里早已没有我什么事了,从这一点讲,我早已退休。另一方面呢,既然我一如既往地做着我喜欢做的事,从这一点讲,我又未尝退休。在我近年的生活中,退休实在是对我影响最微小的一件事。通过阅读经典,我始终生活在人类伟大心灵所建造的那个世界里。这些伟大心灵使我坚定地相信,人的心灵应该是善良、丰富、高贵的。不管现实多么令人失望,每次重温历史上伟大心灵的榜样,我便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在今天的时代,有一些人的灵魂已经彻底堕落,我们不能再指望他们,但是,我们必须指望善的种子会在广大的人心中培育和繁衍,这便是希望之所在。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豆瓣
8.6 (23 个评分)
作者:
(法)加缪
译者:
杜小真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二战后法国有两位号称“精神领袖”的人物,一是萨特,一是加缪。加缪还被称为“法国的良心”,他的散文素以散淡、朴素又寓意深长著称。本书选录了《反与正》和《反叛者》的部分章节,都是人们研究加缪时必会提到的篇章。在《反与正》中,加缪以凝重的笔调回忆了自己的艰苦童年,他的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已有清楚的表现。《反叛者》展开对人生更深入的探索,“光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为什么活着”,他对人生提出的问题和思考,震动着无数人的心灵。
美的覺醒 豆瓣
作者:
蔣勳
遠流
2006
「美的覺醒」演講活動
主 講 人:蔣勳老師
講 題:美的覺醒─蔣勳和你談眼、耳、鼻、舌、身
活動日期:2007年1月13日(六) 14:00-16:45
地 點:中油大樓國光會議廳(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
凡為金石堂網路書店會員免費參加!!(請至遠流博識網報名或洽遠流出版-讀者服務部TEL:23926899轉899)序
廣播是一個有趣的工作。我坐在播音室裡,一個人,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安靜的空氣裡震盪。我很享受這樣的感覺,我很珍惜這樣孤獨的時刻。完全孤獨地與自己的相處。
聲音像潮汐,一波一波,或輕或重,或低沉或飛揚,在空氣裡蕩漾。我好像「看」得見我的聲音,是一種波浪的起伏迴旋。我「看」著我的聲音,像潮汐漲退,包圍著我自己。聲音變成一種安靜的獨白。
也許,有人認為聲音是用來與他人溝通的工具,可是在播音室裡,我覺得聲音首先是自己與自己的獨白。沒有充足的獨白,「溝通」也許只是虛假的來往。我們有太多「call in」「call out」,但是,我們缺乏與自己聲音的對話。沒有聽到自己聲音的迴盪,沒有真實的獨白,太多「call in」「call out」,人其實是最寂寞而空虛的。我聽到了自己的聲音,我「看」到了自己的聲音。
好像月光下粼粼的水的波紋,一圈一圈,緩緩在空氣中盪開。我想用線條勾繪下這舒緩的波紋,像孟克(E.Munch)在「吶喊」畫裡記錄下聲音的波浪。但是聲音的波不只是線條,聲音像一種光,在空氣裡飄飛。
聲音像一種煙,比風還輕的煙,我想用手去承接這煙的重量,一縷一縷,一絲ㄧ絲,我閉著眼睛,感覺煙從指隙間流過,如此柔軟,如此細緻。聲音可以用手去觸摸嗎?
我不經意聽到電視裡一個政客的叫囂,忽然覺得胸口被尖銳的玻璃刺傷,一陣劇痛。聲音可以是母親的手,如此溫暖寬厚;聲音也可以是最銳利的狼牙,殘酷噬咬人最柔軟的心靈。聲音或...MORE>>目錄
自序
尋索美,感覺美
說不清楚的美?
美學的來源
知識不等同感受
解脫知識的負擔
味覺之美
萌芽較早的感官世界
羊大為美?
五種味覺反應
品酒師的考驗
遠離動物的層次
聽覺之美
聽覺的感動力量
找回純粹與美
身體是最美的樂器
沉澱噪音,昇華心靈
自我節制
渴望的象徵
嗅覺之美
一種奇特的提醒
利用嗅覺做判斷
美,是一種智慧
重新儲存美好記憶
不妥協的梅花
智慧從領悟得來
視覺之美
文字語言一無是處
見證生命的存在痕跡
變成文化,形成歷史
看不見的競爭力
辨識形狀
三種造形的母型
觸覺之美
最強的渴望
沉睡的感官重新甦醒
勝過千言萬語
身心中的五感平衡
生命華美地綻放
愈分享,擁有愈多
無目的才會快樂
培養豐美的感官經驗
美:無所不在
莊子哲學
來到美的現場
每一個生命都是一朵花
真正的平等
主 講 人:蔣勳老師
講 題:美的覺醒─蔣勳和你談眼、耳、鼻、舌、身
活動日期:2007年1月13日(六) 14:00-16:45
地 點:中油大樓國光會議廳(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
凡為金石堂網路書店會員免費參加!!(請至遠流博識網報名或洽遠流出版-讀者服務部TEL:23926899轉899)序
廣播是一個有趣的工作。我坐在播音室裡,一個人,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安靜的空氣裡震盪。我很享受這樣的感覺,我很珍惜這樣孤獨的時刻。完全孤獨地與自己的相處。
聲音像潮汐,一波一波,或輕或重,或低沉或飛揚,在空氣裡蕩漾。我好像「看」得見我的聲音,是一種波浪的起伏迴旋。我「看」著我的聲音,像潮汐漲退,包圍著我自己。聲音變成一種安靜的獨白。
也許,有人認為聲音是用來與他人溝通的工具,可是在播音室裡,我覺得聲音首先是自己與自己的獨白。沒有充足的獨白,「溝通」也許只是虛假的來往。我們有太多「call in」「call out」,但是,我們缺乏與自己聲音的對話。沒有聽到自己聲音的迴盪,沒有真實的獨白,太多「call in」「call out」,人其實是最寂寞而空虛的。我聽到了自己的聲音,我「看」到了自己的聲音。
好像月光下粼粼的水的波紋,一圈一圈,緩緩在空氣中盪開。我想用線條勾繪下這舒緩的波紋,像孟克(E.Munch)在「吶喊」畫裡記錄下聲音的波浪。但是聲音的波不只是線條,聲音像一種光,在空氣裡飄飛。
聲音像一種煙,比風還輕的煙,我想用手去承接這煙的重量,一縷一縷,一絲ㄧ絲,我閉著眼睛,感覺煙從指隙間流過,如此柔軟,如此細緻。聲音可以用手去觸摸嗎?
我不經意聽到電視裡一個政客的叫囂,忽然覺得胸口被尖銳的玻璃刺傷,一陣劇痛。聲音可以是母親的手,如此溫暖寬厚;聲音也可以是最銳利的狼牙,殘酷噬咬人最柔軟的心靈。聲音或...MORE>>目錄
自序
尋索美,感覺美
說不清楚的美?
美學的來源
知識不等同感受
解脫知識的負擔
味覺之美
萌芽較早的感官世界
羊大為美?
五種味覺反應
品酒師的考驗
遠離動物的層次
聽覺之美
聽覺的感動力量
找回純粹與美
身體是最美的樂器
沉澱噪音,昇華心靈
自我節制
渴望的象徵
嗅覺之美
一種奇特的提醒
利用嗅覺做判斷
美,是一種智慧
重新儲存美好記憶
不妥協的梅花
智慧從領悟得來
視覺之美
文字語言一無是處
見證生命的存在痕跡
變成文化,形成歷史
看不見的競爭力
辨識形狀
三種造形的母型
觸覺之美
最強的渴望
沉睡的感官重新甦醒
勝過千言萬語
身心中的五感平衡
生命華美地綻放
愈分享,擁有愈多
無目的才會快樂
培養豐美的感官經驗
美:無所不在
莊子哲學
來到美的現場
每一個生命都是一朵花
真正的平等
今生今世 豆瓣 Goodreads
7.9 (10 个评分)
作者:
胡蘭成
遠景出版社
2004
- 9
因我說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張照片,翌日她便取出給我,背後題寫有字:「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裡開出花來。」
她這送照片,好像吳季扎贈劍,依我自己的例來推測,那徐君亦不過是愛悅,卻未必有要的意思。張愛玲是知道我喜愛。你既喜愛,我就給了你,我把相片給你,我亦是歡喜的。而我亦只端然的接受,沒有神魂顛倒......
我與愛玲只是這樣,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厭高,海不厭深,高山大海幾乎不可以是兒女私情。我們兩人都少曾想到要結婚。但英娣竟與我離異,我們才亦結婚了。是年我三十八歲,她二十三歲。我為顧到日後時局變動不致連累她,沒有舉行儀式,只寫婚書為定,文曰:
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上兩句是愛玲撰的,後兩句我撰,旁寫炎櫻為媒證。
--《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胡蘭成
一個生長在貧窮農村的子弟,幼年的時候,癡癡地站在故鄉的橋畔,夢想有一天要越過大河,飛越高山,在紅衫翠袖中,溫香偎玉;和五湖四海的英雄較勁道,比本領。
較勁道,比本領,他徹底被擊敗了。但是他贏得一代佳人的垂青,張愛玲在他落難浪跡天涯時和他結婚。後來他們在錢塘江邊分手,張愛玲回憶這次的生離死別,她說:「那天船將開時,我一個人雨中撐傘站在船舷邊,留著淚,癡癡地望著滔滔的黃浪,不知多久...」
《今生今世》是胡蘭成坎坷一生的自傳。書中,多情的描述了他的生活和愛情。
她這送照片,好像吳季扎贈劍,依我自己的例來推測,那徐君亦不過是愛悅,卻未必有要的意思。張愛玲是知道我喜愛。你既喜愛,我就給了你,我把相片給你,我亦是歡喜的。而我亦只端然的接受,沒有神魂顛倒......
我與愛玲只是這樣,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厭高,海不厭深,高山大海幾乎不可以是兒女私情。我們兩人都少曾想到要結婚。但英娣竟與我離異,我們才亦結婚了。是年我三十八歲,她二十三歲。我為顧到日後時局變動不致連累她,沒有舉行儀式,只寫婚書為定,文曰:
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上兩句是愛玲撰的,後兩句我撰,旁寫炎櫻為媒證。
--《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胡蘭成
一個生長在貧窮農村的子弟,幼年的時候,癡癡地站在故鄉的橋畔,夢想有一天要越過大河,飛越高山,在紅衫翠袖中,溫香偎玉;和五湖四海的英雄較勁道,比本領。
較勁道,比本領,他徹底被擊敗了。但是他贏得一代佳人的垂青,張愛玲在他落難浪跡天涯時和他結婚。後來他們在錢塘江邊分手,張愛玲回憶這次的生離死別,她說:「那天船將開時,我一個人雨中撐傘站在船舷邊,留著淚,癡癡地望著滔滔的黃浪,不知多久...」
《今生今世》是胡蘭成坎坷一生的自傳。書中,多情的描述了他的生活和愛情。
建國新書 豆瓣
作者:
胡蘭成
/
胡兰成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录一则保田与重郎为胡兰成《建国新书》作的序.
保田与重郎(YasudaYojulo,1910-1981)是日本战前战后时期的代表性的右派文艺评论家,是为‘日本浪曼派’(曼字为它故意所用,非误字)的创办人。
由此文可知胡兰成是在保田与重郎的怂恿指点之下,才完成《建国新书》的。此文对胡兰成的思想和文章有相当独到且精辟的分析。
---------------------------------------------
《胡兰成<建国新书>序》(全集第四十卷)
‘我认识胡兰成大人,并不是他还在中国当汪兆铭政权重要阁僚时的事’,故尾崎士郎曾对胡先生的《中国之心》一书所写的序文中,就这么说过。其实,我也是一样。尾崎氏临死之前发表了《山河岁月》,前面就加上了‘为吾友亡命漂泊的孤客胡兰成兄’这样的献词。这个作品描述了战国末期的英雄立花宗茂的传奇性命运。我在这里不打算对尾崎氏的用意作任何的推测,不过,这篇小说中充满了恻恻的幽情。何况《山河岁月》这个书名原来是借用胡先生的同名著作的。尾崎氏生前爱读胡先生的这本书,有意亲自把它翻成日文。我不喜欢随便猜测已故之人的心情,然而,尾崎氏悲痛的隐情是不难想像的。所谓的‘亡命漂泊的孤客’其实是尾崎氏的自寄伤心之辞。胡先生是天性诗人,也是当今东方最高的学人,同时也是没有国家的亡命之客。
先生在年少时已成为革命家,其半生所经历的事,既丰富且多采,畏怖严肃兼而有之,更包含著几分放诞之气,不宜苟且言之。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杰,也是东方文明第一流的学人。我对他文人诗书的天分和文章小说的才能也有极高的评价。这位激进革命家的外表可是古来东方的温容优雅。
对我国国风的真正精神及古道,先生有比国人更深一层的了解,至于其对我国历史民俗或文艺美术的见解,则我值得学习之处颇多。然而,其人依然是忽而变成革命家,终究是个政治之人,我对此一事实有深切的感触。
去年当孙文百年祭典之时,肥后(熊本)的老国士,孙文的亲友柴垣隆翁用独立建了硕大的纪念碑,我也参加了它的典礼。为了那天,孙文哲嗣孙科氏夫妻及哲孙孙子平氏夫妻都从美国远道而来,共襄盛举。而孙子平氏的夫人竟然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追究其罪行的胡先生之义女,这简直是宿缘。当天庆宴上,民国的大使和孙科氏的家族都在贵宾席,而胡先生则坐在我的旁边,算是迎接宾客的东道之一了。宴散后,来宾辞去时,都主动来到胡先生面前殷勤致意,大使则与胡先生握手告别。不过,胡先生仍然是个亡命孤客。
那以前,我听说过有人劝他写一本有关东方风教傅统修身的书。现在东方传统的文明已经濒临灭亡危机。当此之时,能够写这一方面的书的人,恐怕非胡先生莫属吧!因此,我也对那位发案者表示敬意。在熊本的宿舍里,也劝他写这本书,提过我个人的意见。离开熊本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去拜清正公的庙,也在慕清正公而来为他殉死的朝鲜人金官的坟墓上凭吊一番,晚上坐飞机离开熊本,陪先生抵达我在京都的山庄时已是半夜了。
先生似乎从那时开始准备写这本书,也似乎从那时开始考虑放弃政治而从事文笔。在撰述此书之前,他先出版了《心经随喜》,而那正是惊异的政治的书。《心经随喜》是用日语讲演的笔录。
在同一时期,他也开始撰写《建国新书》。他之所以没有写道德方面的书,而特意取名《建国新书》,大概是他所面临的激烈严肃寂寞的现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之故吧!亡命孤客还是需要形成建国的政治理念作为个人道德的根底。不过,祭政一致的体制之下,政治和道德也理应被统一。
这本书是先生用日文撰写的,这使我十分感勤,我们应该好好地体会先生的心情。并且反省自己。先生先用日文写,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我对先生有关日本文学的了解及想法抱有亲密的感情。至于他的文章,因有他独特的想法和见解,很难用世俗的习惯来衡量或调整。认识先生的人,都认为先生的有点辞不达意的日文却具有引发心思的特殊魅力,中文与日文的语法之间有差别,读者应努力去慢慢地体会它。
胡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过亡命到日本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是对古神道有所了解,也说过明治维新的根底也在此。我则认为先生能来到日本对日本历史加上了新的例证。先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流名士,也是第一流的学人,而我国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努力去吸收大陆的第一流文化,且如此加以珍重,永远崇敬,但是,历史的本流上却一次也没有失去过我们古道的精神。在历史的重要时期,外国的伟大人物往往来到日本对我国文明带来了恩惠,为数著实不少。
解释先生所用的词汇时,就可发现此书的中心思想即‘政治’的观念已经用得相当特别。先生此一‘政治’的用法或许将来能扫清当今政治所含有的意义也未可知。至于先生的逻辑,忽而飞跃,忽而燃烧,在其错乱矛盾之中,我看到悲剧之美,而为此心痛。今年的新春,先生撰写一篇奉赞圣德太子的文章,用以阐明我国国体的本义。这是值得日本人学习的,我是这样想。
我自庆祝胡先生能来日本亡命的幸运,用日文撰写这本《建国新书》在同一意义上,也让我感动。不过,想到此事,相对此人,我的感动毋宁是无比的悲痛。
-------------------------------------------------
尾崎士郎(1898-1964)是大众小说家,《人生剧场》为其代表作,他跟胡兰成的关系,待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争时期曾受到军方和国粹主义者的压迫,并不是右派文人。
保田与重郎(YasudaYojulo,1910-1981)是日本战前战后时期的代表性的右派文艺评论家,是为‘日本浪曼派’(曼字为它故意所用,非误字)的创办人。
由此文可知胡兰成是在保田与重郎的怂恿指点之下,才完成《建国新书》的。此文对胡兰成的思想和文章有相当独到且精辟的分析。
---------------------------------------------
《胡兰成<建国新书>序》(全集第四十卷)
‘我认识胡兰成大人,并不是他还在中国当汪兆铭政权重要阁僚时的事’,故尾崎士郎曾对胡先生的《中国之心》一书所写的序文中,就这么说过。其实,我也是一样。尾崎氏临死之前发表了《山河岁月》,前面就加上了‘为吾友亡命漂泊的孤客胡兰成兄’这样的献词。这个作品描述了战国末期的英雄立花宗茂的传奇性命运。我在这里不打算对尾崎氏的用意作任何的推测,不过,这篇小说中充满了恻恻的幽情。何况《山河岁月》这个书名原来是借用胡先生的同名著作的。尾崎氏生前爱读胡先生的这本书,有意亲自把它翻成日文。我不喜欢随便猜测已故之人的心情,然而,尾崎氏悲痛的隐情是不难想像的。所谓的‘亡命漂泊的孤客’其实是尾崎氏的自寄伤心之辞。胡先生是天性诗人,也是当今东方最高的学人,同时也是没有国家的亡命之客。
先生在年少时已成为革命家,其半生所经历的事,既丰富且多采,畏怖严肃兼而有之,更包含著几分放诞之气,不宜苟且言之。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杰,也是东方文明第一流的学人。我对他文人诗书的天分和文章小说的才能也有极高的评价。这位激进革命家的外表可是古来东方的温容优雅。
对我国国风的真正精神及古道,先生有比国人更深一层的了解,至于其对我国历史民俗或文艺美术的见解,则我值得学习之处颇多。然而,其人依然是忽而变成革命家,终究是个政治之人,我对此一事实有深切的感触。
去年当孙文百年祭典之时,肥后(熊本)的老国士,孙文的亲友柴垣隆翁用独立建了硕大的纪念碑,我也参加了它的典礼。为了那天,孙文哲嗣孙科氏夫妻及哲孙孙子平氏夫妻都从美国远道而来,共襄盛举。而孙子平氏的夫人竟然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追究其罪行的胡先生之义女,这简直是宿缘。当天庆宴上,民国的大使和孙科氏的家族都在贵宾席,而胡先生则坐在我的旁边,算是迎接宾客的东道之一了。宴散后,来宾辞去时,都主动来到胡先生面前殷勤致意,大使则与胡先生握手告别。不过,胡先生仍然是个亡命孤客。
那以前,我听说过有人劝他写一本有关东方风教傅统修身的书。现在东方传统的文明已经濒临灭亡危机。当此之时,能够写这一方面的书的人,恐怕非胡先生莫属吧!因此,我也对那位发案者表示敬意。在熊本的宿舍里,也劝他写这本书,提过我个人的意见。离开熊本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去拜清正公的庙,也在慕清正公而来为他殉死的朝鲜人金官的坟墓上凭吊一番,晚上坐飞机离开熊本,陪先生抵达我在京都的山庄时已是半夜了。
先生似乎从那时开始准备写这本书,也似乎从那时开始考虑放弃政治而从事文笔。在撰述此书之前,他先出版了《心经随喜》,而那正是惊异的政治的书。《心经随喜》是用日语讲演的笔录。
在同一时期,他也开始撰写《建国新书》。他之所以没有写道德方面的书,而特意取名《建国新书》,大概是他所面临的激烈严肃寂寞的现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之故吧!亡命孤客还是需要形成建国的政治理念作为个人道德的根底。不过,祭政一致的体制之下,政治和道德也理应被统一。
这本书是先生用日文撰写的,这使我十分感勤,我们应该好好地体会先生的心情。并且反省自己。先生先用日文写,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我对先生有关日本文学的了解及想法抱有亲密的感情。至于他的文章,因有他独特的想法和见解,很难用世俗的习惯来衡量或调整。认识先生的人,都认为先生的有点辞不达意的日文却具有引发心思的特殊魅力,中文与日文的语法之间有差别,读者应努力去慢慢地体会它。
胡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过亡命到日本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是对古神道有所了解,也说过明治维新的根底也在此。我则认为先生能来到日本对日本历史加上了新的例证。先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流名士,也是第一流的学人,而我国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努力去吸收大陆的第一流文化,且如此加以珍重,永远崇敬,但是,历史的本流上却一次也没有失去过我们古道的精神。在历史的重要时期,外国的伟大人物往往来到日本对我国文明带来了恩惠,为数著实不少。
解释先生所用的词汇时,就可发现此书的中心思想即‘政治’的观念已经用得相当特别。先生此一‘政治’的用法或许将来能扫清当今政治所含有的意义也未可知。至于先生的逻辑,忽而飞跃,忽而燃烧,在其错乱矛盾之中,我看到悲剧之美,而为此心痛。今年的新春,先生撰写一篇奉赞圣德太子的文章,用以阐明我国国体的本义。这是值得日本人学习的,我是这样想。
我自庆祝胡先生能来日本亡命的幸运,用日文撰写这本《建国新书》在同一意义上,也让我感动。不过,想到此事,相对此人,我的感动毋宁是无比的悲痛。
-------------------------------------------------
尾崎士郎(1898-1964)是大众小说家,《人生剧场》为其代表作,他跟胡兰成的关系,待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争时期曾受到军方和国粹主义者的压迫,并不是右派文人。
流浪集 豆瓣
作者:
舒国治
大塊
2006
- 10
◆ 流浪
◎當你什麼工作皆不想做,或人生每一樁事皆有極大的不情願,在這時刻,你毋寧去流浪。去千山萬水的熬時度日,耗空你的身心,粗礪你的知覺,直到你能自發的甘願的回抵原先的枯燥崗位做你身前之事。(摘自〈流浪的藝術〉)
◎人總會待在一個地方待得幾乎受不了吧。
與自己熟悉的人相處過久,或許也是一種不道德吧。(摘自〈流浪的藝術〉)
◎太多的人用太多的時光去賺取他原以為很需要卻其實用不太到的錢,以致他連流浪都覺得是奢侈的事了。(摘自〈流浪的藝術〉)
◎最不願意流浪的人,或許是最不願意放掉東西的人。
這就像你約有些朋友,而他永遠不會出來,相當可能他是那種他自己的事是世間最重要事之人。(摘自〈流浪的藝術〉)
◎須知得道高僧亦不時尋覓三兩座安靜寺廟來移換棲身。何也?方丈一室,不宜久居;住持一職,不宜久擁;脫身也,趨幽也,甚至,避禍也。(摘自〈流浪的藝術〉)
◎行李,往往是浪遊不能酣暢的最致命原因。(摘自〈流浪的藝術〉)
◆ 走路
◎走路,是人在宇宙最不受任何情境韁鎖、最得自求多福、最是踽踽尊貴的表現情狀。因能走,你就是天王老子。古時行者訪道;我人能走路流浪,亦不遠矣。(摘自〈流浪的藝術〉)
◎要平常心的對待身體各部位。譬似屁股,哪兒都能安置;沙發可以,岩石上也可以,石階、樹根、草坡、公園鐵凳皆可以。(摘自〈流浪的藝術〉)
◆ 喝茶
◎有時旅行的停歇時機或地點,竟常是因為茶。未必為其美味,乃為其解渴。然而可樂、果汁、礦泉水等亦解渴,何以只特言茶?
這便說到重點。此為茶在某一種微妙感情(家國、歷史、情思、薰陶、年齒………)上最不能教人抵擋之力也。(摘自〈隨遇而飲〉)
◎每日起床,急急忙忙一泡尿。接著如何?便是泡上一杯茶,喝將起來。此外究竟幹得啥事,則不甚記憶。有時想想,人的一生,便在這一泡尿與一杯茶之間度過了。(摘自〈行萬里路,飲無盡茶〉)
◎便因喝茶,判出了一個城市是否宜於人之移動、觀賞、停留。台北市,猶差那麼一點。五十年前的台北,水田廣佈,村意猶濃,光頭長鬚老人與裹小腳老婦猶多,那種時節,樹下稍坐,若有野茶亭,所謂「四方來客、坐片刻無分你我;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者,倒是頗適合的。(摘自〈行萬里路,飲無盡茶〉)
◎這十年茶喝得多了。比在這之前的三、四十年多得多了。
倒不是這十年懂得品茶,實是比較懂得口渴。(摘自〈隨遇而飲〉)
◆ 睡覺
◎睡覺,使眾生終究平等。又睡覺,使眾生在那段時辰終究要平放。噫,這是何奇妙的一樁過程,才見他起高樓,才見他樓塌了,而這一刻,也皆得倒下睡覺。(摘自〈又說睡覺〉)
◎倘若睡得著、睡得暢適舒意神遊太虛、又其實無啥人生屁事,我真樂意一輩子說睡就睡。就像有些少年十八、九歲迷彈吉他,竟是全天候的彈,無止無休,亦是無法無天,蹲馬桶時也抱著它彈。吃飯也忘了,真被叫上飯桌,吃了兩口,放下筷子,取起吉他又繼續撥弄。最後弄到大人已被煩至不堪,幾說出「再彈,我把吉他砸爛!」(摘自〈又說睡覺〉)
◎某些遺世孤立的太古村莊,小孩睡得極多極靜,他們的臉格外平靜,是我們都市倉卒之民難以想像之境景。豈不聞古人詩句「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摘自〈睡〉)
◎曾經想過在小說中可用這樣一句子:「睡一個長覺,睡到錶都停了。」(摘自〈睡覺〉)
◎即使是大人,若能讓自己哭,當是睡眠最好的良藥。但如何能哭呢?最好是看感人的電影。(摘自〈睡覺〉)
◎便因熟睡,許多要緊事竟給睡過了頭,耽誤了。然世上又有哪一件事是真那麼要緊呢?(摘自〈睡覺〉)
◎一個十多歲的初中孩子坐在台灣夏日午後的教室裏,室外是懶懶的炎陽與偶有的不甚甘願拂來的南風,室內是老師的喃喃課語,此一刻也,倘他不會昏昏欲睡,那麼他不是個健康簡單的小孩。(摘自〈睡覺〉)
優雅的浪遊
逢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張瑞芬
2000年以《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驚豔文壇的舒國治,終於在2006年早春,推出讀者引頸企盼的第二本散文集《門外漢的京都》。舒國治的魅力,其實不在題材,而在簡靜的文字與悠閒的意趣。他的旅遊文學屬性,原由1997、1998散文連獲長榮、華航旅行文學獎而來,然而揆諸他《理想的下午》揭櫫的「晃蕩」哲學——「泛看泛聽,淺淺而嚐,漫漫而走」,其實筆下純然是一派安住家居,生活者的氣息,遠非天地遊人的倥傯匆忙。你看他在千年古都尋覓兒時門巷,屋舍寂寂,竹扉半掩,看似舊時台灣鄉下;午夜旅館看黑白老片,猶如60年代台北氛圍重現;夜色中看長牆上孤懸一輪明月,彷彿幼時日本劍道片中場景。簡單來說,《門外漢的京都》猶如家鄉和異地的底片疊合,在他鄉找到了和家相同的質素。場景是京都,可舒國治內心還是那個《台灣重遊》中,趿著拖鞋上夜市擺鹽酥雞攤子的中年歐日桑,很清楚自己是個外人,一點也沒有要融入當地文化的焦灼,反倒有著遠觀的趣味。
這樣的意識,看似遊旅四方,其實台灣在地性格濃厚。世新編導出身,曾經在八年間浪遊美國十數州的舒國治,他的旅遊好比導演到處勘景,聽聲辨位看感覺,屋瓦牆影落日天光都比旅遊指南上的景點重要得多。你瞧他喜孜孜告訴你「京都根本是一座電影的大場景,它一直搬演著『古代』這部電影」;金閣寺別管他的人潮和什麼三島由紀夫了,「只凝視他精緻之極的松、石、島與水上的亭閣」即可。古城三百八十寺,管他收不收門票都只宜張望一下,匆匆經過。某某名剎,簡直的「全寺不值一晒」。明明是玩家也是吃家,他的「門外漢」哲學因此頗有弔詭意趣。放下理性和資訊的焦慮(他甚且不懂日文哩),純任感覺,個人自便,聽不聽也由你。旅館裡的懷石料理繁複精美,吃一口讚一聲,不唯價昂,且工程浩大,實非「尋常像我這樣的阿貓阿狗客人」所能消受;公園旁野餐,川上鶴飛魚游,蘋果熱茶之餘,「倘有幾片cheese,再有一小瓶紅酒,我真他們的想再呆上個把鐘頭」。就像在台北享用高級握壽司後,還非得去啖一碗汕頭牛肉麵,濃重噴香,方足饜飽。住在京都無名小旅店,很像投宿親戚家,「店家的貓在你腳邊看著你換鞋,耳中傳來掌櫃孫女的鋼琴聲」,別有一番情趣。有些人的文字令人欽羨,但也只是欽羨而已,舒國治的文字讓人喜歡,讀者打心裡覺得和他是同類。
舒國治《門外漢的京都》,其實是從《理想的下午》〈城市的氣氛〉一文衍生出來的,無心插柳,展開了一幅淡煙疏雨,留白處處的卷軸。京都古城的旅店長牆、名川美寺,甚至閭巷間的柿果低垂,松枝斜倚,在他筆下無不風情獨具,歷歷如繪。他捨棄厚重綿密的敘述,不貪巨幅,奉行的是「少就是多」、「小即是美」的美學。文字是文言白話的混搭風,雅俗相生,老神在在。〈倘若老來,在京都〉和《理想的下午》中的〈十全老人〉的文言氣,簡直是晚明小品《幽夢影》、《醉古堂劍掃》一路。能讓作家柯裕棻讚譽「內力深厚」、「爐火純青」,可不是太容易的事。楊牧多年前評舒國治得獎小說〈村人遇難記〉就道破天機,說他的文字「聲東擊西」,「看似淡漠鬆弛,實則充滿藝術張力」。《門外漢的京都》中言京都老舊旅店,甬道登樓可聽木頭軋吱聲,進進出出,穿穿脫脫,「此種住店,又豈是住西洋式大飯店銅牆鐵壁甬道陰森與要洗澡只走兩步在自己房內快速沖滌便即刻完成等過度便捷似飄忽無痕啥也沒留心上所能比擬」。這種辨識度極高,誰也學不來仿不像的風格又是啥人可以比擬?
讀《門外漢的京都》,宜把前些時馬可孛羅出版的壽岳章子《千年繁華》、《喜樂京都》翻出重看,一個以千年古風抵拒現代文明的城市,專出那些百年掃帚店、草鞋店、第16代剪刀舖、做榻榻米的頑固老爹。庭園小石步道步步為營,藏青色浴衣有著壓抑之美。和果子店名「嵯峨野之月」、「葛之初花」,女人低首穿著木屐,撐著小雨傘走過長巷。懷念兒時舊事的壽岳章子,和步行晃蕩的外來者舒國治,共築了牆裡牆外的人生。美國小說家愛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在《巴黎晃遊者》中說:「晃遊者的定義就是閒暇極多的人」。班雅明更說:晃遊者尋找的是經驗而非知識。浪遊達人的龜毛藝術,豈僅優雅而已。摩挲著《門外漢的京都》一書封面,彷彿聞得到杉木的冷香與質感,如果書本也有氣場,這臥遊便無疑是一場芳美的森淋浴,使人通體適暢。
舒國治的晃蕩,是城市裡恍惚的慢板,優雅的浪遊。從容緩步,以自身經驗為中心,六經皆我(的經驗的)註腳。有著收入《七○年代懺情錄》的〈台北遊藝〉為基底,舒國治的「台北城居」系列,無疑是讀者心中下一個值得期待的人生目標,那絕對是和朱天心各顯神通的另一種漫遊台北的方式。
(原載於《文訊》2006年4月)
◎當你什麼工作皆不想做,或人生每一樁事皆有極大的不情願,在這時刻,你毋寧去流浪。去千山萬水的熬時度日,耗空你的身心,粗礪你的知覺,直到你能自發的甘願的回抵原先的枯燥崗位做你身前之事。(摘自〈流浪的藝術〉)
◎人總會待在一個地方待得幾乎受不了吧。
與自己熟悉的人相處過久,或許也是一種不道德吧。(摘自〈流浪的藝術〉)
◎太多的人用太多的時光去賺取他原以為很需要卻其實用不太到的錢,以致他連流浪都覺得是奢侈的事了。(摘自〈流浪的藝術〉)
◎最不願意流浪的人,或許是最不願意放掉東西的人。
這就像你約有些朋友,而他永遠不會出來,相當可能他是那種他自己的事是世間最重要事之人。(摘自〈流浪的藝術〉)
◎須知得道高僧亦不時尋覓三兩座安靜寺廟來移換棲身。何也?方丈一室,不宜久居;住持一職,不宜久擁;脫身也,趨幽也,甚至,避禍也。(摘自〈流浪的藝術〉)
◎行李,往往是浪遊不能酣暢的最致命原因。(摘自〈流浪的藝術〉)
◆ 走路
◎走路,是人在宇宙最不受任何情境韁鎖、最得自求多福、最是踽踽尊貴的表現情狀。因能走,你就是天王老子。古時行者訪道;我人能走路流浪,亦不遠矣。(摘自〈流浪的藝術〉)
◎要平常心的對待身體各部位。譬似屁股,哪兒都能安置;沙發可以,岩石上也可以,石階、樹根、草坡、公園鐵凳皆可以。(摘自〈流浪的藝術〉)
◆ 喝茶
◎有時旅行的停歇時機或地點,竟常是因為茶。未必為其美味,乃為其解渴。然而可樂、果汁、礦泉水等亦解渴,何以只特言茶?
這便說到重點。此為茶在某一種微妙感情(家國、歷史、情思、薰陶、年齒………)上最不能教人抵擋之力也。(摘自〈隨遇而飲〉)
◎每日起床,急急忙忙一泡尿。接著如何?便是泡上一杯茶,喝將起來。此外究竟幹得啥事,則不甚記憶。有時想想,人的一生,便在這一泡尿與一杯茶之間度過了。(摘自〈行萬里路,飲無盡茶〉)
◎便因喝茶,判出了一個城市是否宜於人之移動、觀賞、停留。台北市,猶差那麼一點。五十年前的台北,水田廣佈,村意猶濃,光頭長鬚老人與裹小腳老婦猶多,那種時節,樹下稍坐,若有野茶亭,所謂「四方來客、坐片刻無分你我;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者,倒是頗適合的。(摘自〈行萬里路,飲無盡茶〉)
◎這十年茶喝得多了。比在這之前的三、四十年多得多了。
倒不是這十年懂得品茶,實是比較懂得口渴。(摘自〈隨遇而飲〉)
◆ 睡覺
◎睡覺,使眾生終究平等。又睡覺,使眾生在那段時辰終究要平放。噫,這是何奇妙的一樁過程,才見他起高樓,才見他樓塌了,而這一刻,也皆得倒下睡覺。(摘自〈又說睡覺〉)
◎倘若睡得著、睡得暢適舒意神遊太虛、又其實無啥人生屁事,我真樂意一輩子說睡就睡。就像有些少年十八、九歲迷彈吉他,竟是全天候的彈,無止無休,亦是無法無天,蹲馬桶時也抱著它彈。吃飯也忘了,真被叫上飯桌,吃了兩口,放下筷子,取起吉他又繼續撥弄。最後弄到大人已被煩至不堪,幾說出「再彈,我把吉他砸爛!」(摘自〈又說睡覺〉)
◎某些遺世孤立的太古村莊,小孩睡得極多極靜,他們的臉格外平靜,是我們都市倉卒之民難以想像之境景。豈不聞古人詩句「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摘自〈睡〉)
◎曾經想過在小說中可用這樣一句子:「睡一個長覺,睡到錶都停了。」(摘自〈睡覺〉)
◎即使是大人,若能讓自己哭,當是睡眠最好的良藥。但如何能哭呢?最好是看感人的電影。(摘自〈睡覺〉)
◎便因熟睡,許多要緊事竟給睡過了頭,耽誤了。然世上又有哪一件事是真那麼要緊呢?(摘自〈睡覺〉)
◎一個十多歲的初中孩子坐在台灣夏日午後的教室裏,室外是懶懶的炎陽與偶有的不甚甘願拂來的南風,室內是老師的喃喃課語,此一刻也,倘他不會昏昏欲睡,那麼他不是個健康簡單的小孩。(摘自〈睡覺〉)
優雅的浪遊
逢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張瑞芬
2000年以《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驚豔文壇的舒國治,終於在2006年早春,推出讀者引頸企盼的第二本散文集《門外漢的京都》。舒國治的魅力,其實不在題材,而在簡靜的文字與悠閒的意趣。他的旅遊文學屬性,原由1997、1998散文連獲長榮、華航旅行文學獎而來,然而揆諸他《理想的下午》揭櫫的「晃蕩」哲學——「泛看泛聽,淺淺而嚐,漫漫而走」,其實筆下純然是一派安住家居,生活者的氣息,遠非天地遊人的倥傯匆忙。你看他在千年古都尋覓兒時門巷,屋舍寂寂,竹扉半掩,看似舊時台灣鄉下;午夜旅館看黑白老片,猶如60年代台北氛圍重現;夜色中看長牆上孤懸一輪明月,彷彿幼時日本劍道片中場景。簡單來說,《門外漢的京都》猶如家鄉和異地的底片疊合,在他鄉找到了和家相同的質素。場景是京都,可舒國治內心還是那個《台灣重遊》中,趿著拖鞋上夜市擺鹽酥雞攤子的中年歐日桑,很清楚自己是個外人,一點也沒有要融入當地文化的焦灼,反倒有著遠觀的趣味。
這樣的意識,看似遊旅四方,其實台灣在地性格濃厚。世新編導出身,曾經在八年間浪遊美國十數州的舒國治,他的旅遊好比導演到處勘景,聽聲辨位看感覺,屋瓦牆影落日天光都比旅遊指南上的景點重要得多。你瞧他喜孜孜告訴你「京都根本是一座電影的大場景,它一直搬演著『古代』這部電影」;金閣寺別管他的人潮和什麼三島由紀夫了,「只凝視他精緻之極的松、石、島與水上的亭閣」即可。古城三百八十寺,管他收不收門票都只宜張望一下,匆匆經過。某某名剎,簡直的「全寺不值一晒」。明明是玩家也是吃家,他的「門外漢」哲學因此頗有弔詭意趣。放下理性和資訊的焦慮(他甚且不懂日文哩),純任感覺,個人自便,聽不聽也由你。旅館裡的懷石料理繁複精美,吃一口讚一聲,不唯價昂,且工程浩大,實非「尋常像我這樣的阿貓阿狗客人」所能消受;公園旁野餐,川上鶴飛魚游,蘋果熱茶之餘,「倘有幾片cheese,再有一小瓶紅酒,我真他們的想再呆上個把鐘頭」。就像在台北享用高級握壽司後,還非得去啖一碗汕頭牛肉麵,濃重噴香,方足饜飽。住在京都無名小旅店,很像投宿親戚家,「店家的貓在你腳邊看著你換鞋,耳中傳來掌櫃孫女的鋼琴聲」,別有一番情趣。有些人的文字令人欽羨,但也只是欽羨而已,舒國治的文字讓人喜歡,讀者打心裡覺得和他是同類。
舒國治《門外漢的京都》,其實是從《理想的下午》〈城市的氣氛〉一文衍生出來的,無心插柳,展開了一幅淡煙疏雨,留白處處的卷軸。京都古城的旅店長牆、名川美寺,甚至閭巷間的柿果低垂,松枝斜倚,在他筆下無不風情獨具,歷歷如繪。他捨棄厚重綿密的敘述,不貪巨幅,奉行的是「少就是多」、「小即是美」的美學。文字是文言白話的混搭風,雅俗相生,老神在在。〈倘若老來,在京都〉和《理想的下午》中的〈十全老人〉的文言氣,簡直是晚明小品《幽夢影》、《醉古堂劍掃》一路。能讓作家柯裕棻讚譽「內力深厚」、「爐火純青」,可不是太容易的事。楊牧多年前評舒國治得獎小說〈村人遇難記〉就道破天機,說他的文字「聲東擊西」,「看似淡漠鬆弛,實則充滿藝術張力」。《門外漢的京都》中言京都老舊旅店,甬道登樓可聽木頭軋吱聲,進進出出,穿穿脫脫,「此種住店,又豈是住西洋式大飯店銅牆鐵壁甬道陰森與要洗澡只走兩步在自己房內快速沖滌便即刻完成等過度便捷似飄忽無痕啥也沒留心上所能比擬」。這種辨識度極高,誰也學不來仿不像的風格又是啥人可以比擬?
讀《門外漢的京都》,宜把前些時馬可孛羅出版的壽岳章子《千年繁華》、《喜樂京都》翻出重看,一個以千年古風抵拒現代文明的城市,專出那些百年掃帚店、草鞋店、第16代剪刀舖、做榻榻米的頑固老爹。庭園小石步道步步為營,藏青色浴衣有著壓抑之美。和果子店名「嵯峨野之月」、「葛之初花」,女人低首穿著木屐,撐著小雨傘走過長巷。懷念兒時舊事的壽岳章子,和步行晃蕩的外來者舒國治,共築了牆裡牆外的人生。美國小說家愛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在《巴黎晃遊者》中說:「晃遊者的定義就是閒暇極多的人」。班雅明更說:晃遊者尋找的是經驗而非知識。浪遊達人的龜毛藝術,豈僅優雅而已。摩挲著《門外漢的京都》一書封面,彷彿聞得到杉木的冷香與質感,如果書本也有氣場,這臥遊便無疑是一場芳美的森淋浴,使人通體適暢。
舒國治的晃蕩,是城市裡恍惚的慢板,優雅的浪遊。從容緩步,以自身經驗為中心,六經皆我(的經驗的)註腳。有著收入《七○年代懺情錄》的〈台北遊藝〉為基底,舒國治的「台北城居」系列,無疑是讀者心中下一個值得期待的人生目標,那絕對是和朱天心各顯神通的另一種漫遊台北的方式。
(原載於《文訊》2006年4月)
世間的名字 豆瓣 Goodreads
作者:
唐諾
INK印刻出版公司
2011
- 1
這一次,不談書,不寫導讀,還原為散文家唐諾自身。
近取諸身:哥哥、同學與編輯;
遠取諸物:富翁、網球手與拉麵師傅。
深度就在表面,名字即是實相。
是最具企圖,也最深情的一次命名。
這一次,將以下身分打碎和泥重塑:編輯、球評、推理小說導讀、業餘古文字愛好者、專業讀書人、博學雜食者、小說家的教練、大導演的諍友……,還原為書寫者唐諾自身,專注如刺蝟,通達似狐狸,言志兼抒情,雄辯亦溫柔。在台灣,很久沒有看見這種「強悍而美麗」的大散文,旁徵博引卻不枯燥乏味,冷眼嘲諷底下有著一副熱心腸,時而深沉曲繞,不厭其煩再三辯證;時而直抒胸臆,用起大白話,字字句句鑿進你心坎底。
這一次,不談書,不特地談一本書;不評論作家,不為他人作嫁;不依傍一種主義,不主張一樣學說;主角不是班雅明、不是卡爾維諾、不是朱天文,也不是波赫士(雖則總如暗夜中忽明忽滅地螢火蟲縈繞不去),眾神退散,撥雲見日,走來的是這樣一個謙卑之人:「是為了看懂,多看懂一些,而不是成為。」──〈棋士〉。
這一次,是唐諾最無邊界、無框限的一次書寫。雕刻時光,近取諸身:如〈哥哥〉、〈同學與家人〉、〈少尉〉、〈編輯〉、〈小說家〉。
「我們這些可能是最後一個世代還擁有成排兄弟姊妹的人,不會不知道如今所謂的兄弟姊妹大致是怎麼回事,比水濃比水密度高的東西遍地都是,大家就別裝了吧,通常幸福無間的時日不會長過童年,如同梅特靈克的青鳥般是某種無法存活於現實天光和人生真相的東西。隨著各自童年結束,接下來便是一晃幾十年逐步淡漠稀薄下去、行禮如儀但毋甯只是義務的拖行歲月,最終正式斷裂於父母親的衰老死去,彷彿父母是水落石出之後僅剩的聯繫,這共有的源頭一旦消失了,我們也就回復成無關係的人,並偷偷在心裡鬆了口氣。」──〈哥哥〉
「書籍這麼個寒傖的行業,會在其末端呈現著如此繁花盛開的驚人模樣,我想不出來有其他任何一個領域,能如此深如此廣同時如此多樣如此精密──人類的思維,包括每一種想法,每一個念頭,每一次夢境,管它多細瑣、多奇怪、多私密、多不合時宜,乃至於多幽黯恐怖邪惡,你在世界其他任一個領域任一個角落就算不危險,也無不撞得鼻青眼腫,便只有在書籍這個世界中,每一種你都有機會找到實踐的可能,有機會碰到某一個還肯一試,並負責編好它、送它到讀者面前的傻編輯;也就是說,除了你自己容量有限又時時遭受遺忘威脅的記憶力之外,如果說這個世界還有一處可容身可收存可展示的地方,並鄭重相待,那必定是書籍了。」──〈編輯〉
觸類旁通,遠取諸物:如〈富翁〉、〈醫生〉、〈主播〉、〈神〉。
「我想人長得太好看,在人人稱羨同時必定是很辛苦的,是上天一個不懷好意的祝福,特別是在如今這個鋪天蓋地獵殺俊男美女的時代。如今,美麗已不只是要件了(你會唱歌而且你必須美麗,你會鑑識凶器上的微量DNA而且你必須美麗云云),美麗還單獨成立不必再配備其他任何能力,也就是說,你什麼都不必做不必會,你就每天廿四小時在那裡美麗就行了。這其實就是今天台灣所謂『名模』的真正定義,她們不是歌手、不是演員、甚至不用走伸展台(台灣沒什麼時裝工業可言),她們就只是自身的存在而已,存在即真理──很抱歉,這讓我又忍不住想到錢鍾書,《圍城》,寫方鴻漸從歐陸回國的船上,長日漫漫窮極無聊,他們為那名成天穿著泳裝賣弄風情的可敬女士取了個綽號就叫『真理』,因為『真理是赤裸裸的』,但仔細想想這不太對,決定改稱呼她『局部的真理』。」──〈主播〉
「看守生死的界線,不等於就是人生命和死亡的詮釋者指導者,一如哨兵不自動等於哲學家,這樣的誤會對雙方大家都不好。醫學,最終是一門專業手藝;醫生,是修護者而不是建造者。不要惑於語言的暗示性,修護工作不見得比創造工作不高貴,事實上,它更綿密更時時發生,要談公益性,它也更能實質幫到更多急切的人更富光輝,因此,更需要專注不是嗎?就像葛林筆下那位讓他都折服的麻瘋病醫生柯林。」──〈醫生〉
多識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彷彿各行各業,百工技藝之浮世繪,如:〈拉麵師傅〉、〈棋士〉、〈書家〉、〈網球手與吟遊詩人〉
「甚久以來,我一直無法妥善解釋自己一個童稚味十足的心理,因為羽生而學將棋,因為吳清源而下圍棋,因為費德勒而看網球,因為愛因斯坦而讀物理學,因為波赫士而讀詩,還有賈西亞.馬奎茲(或直接就是《一百年的孤寂》)之於小說,李維-史陀之於神話學云云,我總是因為目睹著某個神奇的人、神奇的事物從而進入某一領域展開學習。」──〈棋士〉
「六百到一千二的價格限定,進一步蒸發掉夢的胡思亂想多餘成分,濃縮出夢樸素、辛勤、真實不欺、因拉麵而拉麵這部分;驅走了表演者,留下了拉麵師傅──我們看哈利.溫斯頓的珠寶店,皇宮一樣門口站著警衛,店裡四時清涼無汗如佛家的不思議之國,店員永遠比顧客多,也通常比顧客優雅美麗,夢在此地有無盡寬敞舒服的空間可伸展可徘徊;但一家做得下去的拉麵店需要川流不息的顧客,爐子煉獄之火般永不熄滅,甩麵水讓兩腳站立之地永遠濕漉漉的,接近我們所說的水深火熱,各等各色的人壅塞大聲講話還在門外排隊,工作跟打仗一樣,不,跟打仗不一樣,士兵要戰火完全停歇才清理戰場並把大部分工作留給大自然自己分解,拉麵店是一邊打一邊得搶時間收拾滿桌油膩狼藉的盤碗,夢在此地匆忙、費力、狹窄而且揮汗如雨。」──〈拉麵師傅〉
馬奎斯說:「這個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去指。」
書寫者唐諾,用其堅定不懈的筆,一一為我們指出「世間的名字」,深度就在表面,名字即是實相,是最具企圖,也最深情的一次「命名」。
近取諸身:哥哥、同學與編輯;
遠取諸物:富翁、網球手與拉麵師傅。
深度就在表面,名字即是實相。
是最具企圖,也最深情的一次命名。
這一次,將以下身分打碎和泥重塑:編輯、球評、推理小說導讀、業餘古文字愛好者、專業讀書人、博學雜食者、小說家的教練、大導演的諍友……,還原為書寫者唐諾自身,專注如刺蝟,通達似狐狸,言志兼抒情,雄辯亦溫柔。在台灣,很久沒有看見這種「強悍而美麗」的大散文,旁徵博引卻不枯燥乏味,冷眼嘲諷底下有著一副熱心腸,時而深沉曲繞,不厭其煩再三辯證;時而直抒胸臆,用起大白話,字字句句鑿進你心坎底。
這一次,不談書,不特地談一本書;不評論作家,不為他人作嫁;不依傍一種主義,不主張一樣學說;主角不是班雅明、不是卡爾維諾、不是朱天文,也不是波赫士(雖則總如暗夜中忽明忽滅地螢火蟲縈繞不去),眾神退散,撥雲見日,走來的是這樣一個謙卑之人:「是為了看懂,多看懂一些,而不是成為。」──〈棋士〉。
這一次,是唐諾最無邊界、無框限的一次書寫。雕刻時光,近取諸身:如〈哥哥〉、〈同學與家人〉、〈少尉〉、〈編輯〉、〈小說家〉。
「我們這些可能是最後一個世代還擁有成排兄弟姊妹的人,不會不知道如今所謂的兄弟姊妹大致是怎麼回事,比水濃比水密度高的東西遍地都是,大家就別裝了吧,通常幸福無間的時日不會長過童年,如同梅特靈克的青鳥般是某種無法存活於現實天光和人生真相的東西。隨著各自童年結束,接下來便是一晃幾十年逐步淡漠稀薄下去、行禮如儀但毋甯只是義務的拖行歲月,最終正式斷裂於父母親的衰老死去,彷彿父母是水落石出之後僅剩的聯繫,這共有的源頭一旦消失了,我們也就回復成無關係的人,並偷偷在心裡鬆了口氣。」──〈哥哥〉
「書籍這麼個寒傖的行業,會在其末端呈現著如此繁花盛開的驚人模樣,我想不出來有其他任何一個領域,能如此深如此廣同時如此多樣如此精密──人類的思維,包括每一種想法,每一個念頭,每一次夢境,管它多細瑣、多奇怪、多私密、多不合時宜,乃至於多幽黯恐怖邪惡,你在世界其他任一個領域任一個角落就算不危險,也無不撞得鼻青眼腫,便只有在書籍這個世界中,每一種你都有機會找到實踐的可能,有機會碰到某一個還肯一試,並負責編好它、送它到讀者面前的傻編輯;也就是說,除了你自己容量有限又時時遭受遺忘威脅的記憶力之外,如果說這個世界還有一處可容身可收存可展示的地方,並鄭重相待,那必定是書籍了。」──〈編輯〉
觸類旁通,遠取諸物:如〈富翁〉、〈醫生〉、〈主播〉、〈神〉。
「我想人長得太好看,在人人稱羨同時必定是很辛苦的,是上天一個不懷好意的祝福,特別是在如今這個鋪天蓋地獵殺俊男美女的時代。如今,美麗已不只是要件了(你會唱歌而且你必須美麗,你會鑑識凶器上的微量DNA而且你必須美麗云云),美麗還單獨成立不必再配備其他任何能力,也就是說,你什麼都不必做不必會,你就每天廿四小時在那裡美麗就行了。這其實就是今天台灣所謂『名模』的真正定義,她們不是歌手、不是演員、甚至不用走伸展台(台灣沒什麼時裝工業可言),她們就只是自身的存在而已,存在即真理──很抱歉,這讓我又忍不住想到錢鍾書,《圍城》,寫方鴻漸從歐陸回國的船上,長日漫漫窮極無聊,他們為那名成天穿著泳裝賣弄風情的可敬女士取了個綽號就叫『真理』,因為『真理是赤裸裸的』,但仔細想想這不太對,決定改稱呼她『局部的真理』。」──〈主播〉
「看守生死的界線,不等於就是人生命和死亡的詮釋者指導者,一如哨兵不自動等於哲學家,這樣的誤會對雙方大家都不好。醫學,最終是一門專業手藝;醫生,是修護者而不是建造者。不要惑於語言的暗示性,修護工作不見得比創造工作不高貴,事實上,它更綿密更時時發生,要談公益性,它也更能實質幫到更多急切的人更富光輝,因此,更需要專注不是嗎?就像葛林筆下那位讓他都折服的麻瘋病醫生柯林。」──〈醫生〉
多識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彷彿各行各業,百工技藝之浮世繪,如:〈拉麵師傅〉、〈棋士〉、〈書家〉、〈網球手與吟遊詩人〉
「甚久以來,我一直無法妥善解釋自己一個童稚味十足的心理,因為羽生而學將棋,因為吳清源而下圍棋,因為費德勒而看網球,因為愛因斯坦而讀物理學,因為波赫士而讀詩,還有賈西亞.馬奎茲(或直接就是《一百年的孤寂》)之於小說,李維-史陀之於神話學云云,我總是因為目睹著某個神奇的人、神奇的事物從而進入某一領域展開學習。」──〈棋士〉
「六百到一千二的價格限定,進一步蒸發掉夢的胡思亂想多餘成分,濃縮出夢樸素、辛勤、真實不欺、因拉麵而拉麵這部分;驅走了表演者,留下了拉麵師傅──我們看哈利.溫斯頓的珠寶店,皇宮一樣門口站著警衛,店裡四時清涼無汗如佛家的不思議之國,店員永遠比顧客多,也通常比顧客優雅美麗,夢在此地有無盡寬敞舒服的空間可伸展可徘徊;但一家做得下去的拉麵店需要川流不息的顧客,爐子煉獄之火般永不熄滅,甩麵水讓兩腳站立之地永遠濕漉漉的,接近我們所說的水深火熱,各等各色的人壅塞大聲講話還在門外排隊,工作跟打仗一樣,不,跟打仗不一樣,士兵要戰火完全停歇才清理戰場並把大部分工作留給大自然自己分解,拉麵店是一邊打一邊得搶時間收拾滿桌油膩狼藉的盤碗,夢在此地匆忙、費力、狹窄而且揮汗如雨。」──〈拉麵師傅〉
馬奎斯說:「這個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去指。」
書寫者唐諾,用其堅定不懈的筆,一一為我們指出「世間的名字」,深度就在表面,名字即是實相,是最具企圖,也最深情的一次「命名」。
泽泻集 过去的生命 豆瓣
作者:
周作人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1
《泽泻集》序
近几年来我才学写文章,但是成绩不很佳。因为出身贫贱,幼时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后来所学的本业又与文学完全无缘,想来写什么批评文字,非但是身分不相应,也实在是徒劳的事。这个自觉却是不久就得到,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有友人问及,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我惭愧无以应。但是转侧一想,虽然够不上说好,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昧的,也还有三五篇,现在便把他搜集起来,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戈尔特堡(Isaac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至于书名泽泻,那也别无深意,——并不一定用《楚辞》的“筐泽泻以豹鞹兮”的意思,不过因为喜欢这种小草,所以用作书名罢了。在日本的“纹章”里也有泽泻,现在就借用这个图案放在卷首。
十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
(1927年8月刊《语丝》145期,署名起明)
《过去的生命》序
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其中二十六篇,曾收在《雪朝》第二集中,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就用了第十二篇《过去的生命》做了全书的名字。
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缘故,我觉得还可以把他收入《苦雨斋小书》的里边,未必是什么敝帚自珍的意思,若是献丑狂(Exhibitionism)呢,那与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样,多少怕有一点儿罢?
书面图案系借用库普加(FrankKupka)的画,题曰《生命》。我是不懂美术的,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叫做什么Orphism,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近几年来我才学写文章,但是成绩不很佳。因为出身贫贱,幼时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后来所学的本业又与文学完全无缘,想来写什么批评文字,非但是身分不相应,也实在是徒劳的事。这个自觉却是不久就得到,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有友人问及,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我惭愧无以应。但是转侧一想,虽然够不上说好,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昧的,也还有三五篇,现在便把他搜集起来,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戈尔特堡(Isaac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至于书名泽泻,那也别无深意,——并不一定用《楚辞》的“筐泽泻以豹鞹兮”的意思,不过因为喜欢这种小草,所以用作书名罢了。在日本的“纹章”里也有泽泻,现在就借用这个图案放在卷首。
十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
(1927年8月刊《语丝》145期,署名起明)
《过去的生命》序
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其中二十六篇,曾收在《雪朝》第二集中,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就用了第十二篇《过去的生命》做了全书的名字。
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缘故,我觉得还可以把他收入《苦雨斋小书》的里边,未必是什么敝帚自珍的意思,若是献丑狂(Exhibitionism)呢,那与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样,多少怕有一点儿罢?
书面图案系借用库普加(FrankKupka)的画,题曰《生命》。我是不懂美术的,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叫做什么Orphism,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周作人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