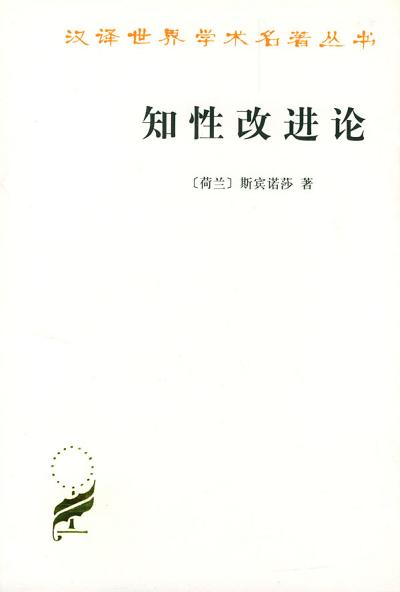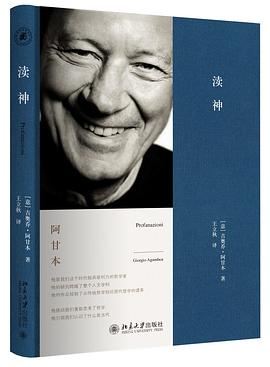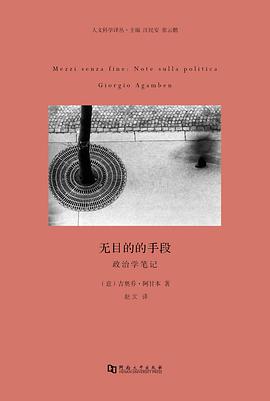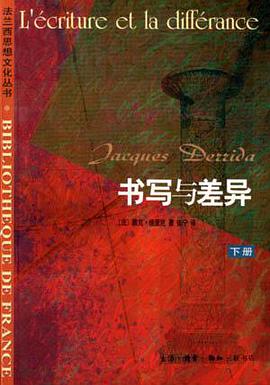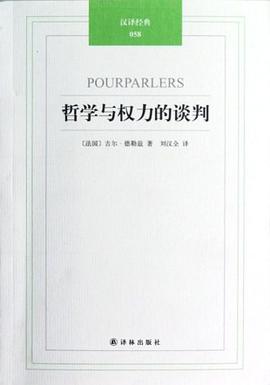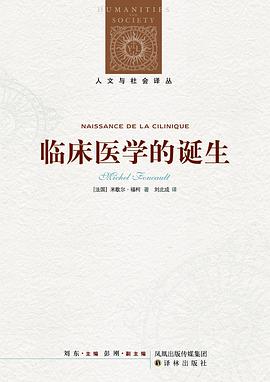哲学
知性改进论 豆瓣
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Et de via, Qua Optime in Veram Rerum Cognitionem Dirigitur
8.0 (10 个评分)
作者:
[荷兰] 巴鲁赫·斯宾诺莎
译者:
贺麟
商务印书馆
1960
- 2
斯宾诺莎(1632—1677)是荷兰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理性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知性改进论》是斯宾诺莎最早的一部著作,篇幅不大,副标题为“并论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斯宾诺莎在书中探讨了寻求知识的途径和方法,指出真理和实在的系统一贯性,并力图把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力学和数学的精神推广应用到研究存在的认识的整个领域。
物体系 豆瓣
Le Système des objets
8.3 (12 个评分)
作者:
[法]让·鲍德里亚
译者:
林志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1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物品的身影。可以说,我们的所有活动都跟物品有关。鲍德里亚试图对种类繁多的物品加以区分,并勾勒出一个物品的层级与体系。鲍德里亚认为,现代家具代表一种系列,而古旧物品或者极其昂贵的奢侈品则代表模范。普通人因为居住空间有限,只能选择可随意折叠、拆卸的现代系列家具,而只有少数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笨重、华丽的实木古典家具。
系列与模范的区分实际上是人的阶层的区分,是普通人和富人的区分,也是一种符号和语言。对于那些资金有限又想占有奢侈品的人来说,分期付款或者信用贷款则是一种福音。过去先积攒财富,再购买奢侈品的模式被抛弃了,靠预期收入先行占有奢侈品的做法广为流行。当下,无所不在的广告依靠关心人的情怀推销各种模范、品牌。物品变成了一种消费能力的符号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出于自由选择的购买因为消耗了未来预期的收入和生命而使人变得不自由。于是,人们生产物品、消费物品,最终却被物品所奴役,被物品背后的资本所奴役。
系列与模范的区分实际上是人的阶层的区分,是普通人和富人的区分,也是一种符号和语言。对于那些资金有限又想占有奢侈品的人来说,分期付款或者信用贷款则是一种福音。过去先积攒财富,再购买奢侈品的模式被抛弃了,靠预期收入先行占有奢侈品的做法广为流行。当下,无所不在的广告依靠关心人的情怀推销各种模范、品牌。物品变成了一种消费能力的符号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出于自由选择的购买因为消耗了未来预期的收入和生命而使人变得不自由。于是,人们生产物品、消费物品,最终却被物品所奴役,被物品背后的资本所奴役。
日常生活的革命 豆瓣
作者:
[法] 鲁尔·瓦纳格姆
译者:
张新木 戴秋霞
/
王也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0
本书是法国著名学者、境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瓦纳格姆论日常生活的一部名著。“日常生活的革命”绝对超越了词语本身,因为这一绝对免疫于同化的理由。它抓住了我们所有人(甚至是我们中最愚蠢的人)都意识到但却无能为力的生活的主要问题:一种挥之不去的空虚感,一个应该是“有”的“无”。这是瓦纳格姆的魔力所在。他知道它的真正原因,他正当地指控我们长时间地忽略了社会秩序及其所引起的疏离,他鼓动我们猛烈地反叛,快乐地自杀;首先是要集体革命,来终结所有的孤独与倦怠。瓦纳格姆不仅是一位政治革命者,他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投身于词语与行动的人。根本说来,他是他自己,对我们来说,这足以完全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瓦纳格姆不需要跟随者,不需要偶像崇拜,他希望每个人真正去要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本热情洋溢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大段大段的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主将的言论。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豆瓣
Gilbert Simondon
作者:
Gilbert Simondon
译者:
John Rogove
Univocal Publishing
2017
- 4
Few thinkers have been as influential upon current discussions and theoretical practices in the age of media archaeolog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digital humanities as the French thinker Gilbert Simondon. Simondon’s prolific intellectual curiosity led his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reflections to traverse a variety of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ing philosophy, psychology, the beginnings of cybernetic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religion. For Simondon, the human/machine distinction is perhaps not a simple dichotomy. There i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our technical objects, and while it has been said that humans have an alienating rapport with technical objects, Simondon takes up the task of a true thinker who sees the potential for humanity to uncover life-affirming modes of technical objects whereby we can discover potentiality for novel, healthful, and dis-alienating rapports with them. For Simondon, by way of studying its genesis, one must grant to the technical object the same ontological status as that of the aesthetic object or even a living being. His work thus opens up exciting new entry points into studying the human’s rapport with its continually changing technical reality. This first complete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of Gilbert Simondon’s groundbreaking and influential work finally presents to Anglophone readers one of the pinnacle works of France’s most unique thinkers of technics.
神圣人 豆瓣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8.4 (23 个评分)
作者:
[意大利] 吉奥乔·阿甘本
译者:
吴冠军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 7
◆阿甘本成名作首度中文译介
◆“神圣人”生命政治系列的开篇之作
◆无可争议的政治哲学经典名著
【内容简介】
在《神圣人》中,阿甘本旨在把关于纯粹可能性、潜在性与权力的问题,同政治与社会伦理的问题在以下语境中连接起来:后者已丧失其早前的宗教、形而上学与文化的立基。阿甘本从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碎片性分析中获得启示,进而以巨大的广度、强度与敏锐度,在传统政治理论史中探查关于一种生命权力理念的隐秘在场。他指出,从政治理论的最早论题(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论述)开始,并且在整个关于主权(无论是国王还是国家)的西方思想史中,主权作为一种针对“生命”的权力的理念,始终隐秘存在。
阿甘本认为,这一理念始终保持纯然隐在的原因,在于神圣之域(或者说神圣性的理念)同主权的理念紧密关联的方式。阿甘本的研究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卡尔·施米特认为,主权者的状态乃是其所守卫的诸种规范的例外;人类学的研究已揭示神圣之域同禁忌之间的紧密交链。在此两者之上,阿甘本将神圣之人定义为那种能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人;在他看来,这个悖论性的人物恰恰仍活跃在现代个体的状态中——现代个体生活在一个对所有个体的集体性“赤裸生命”施加严密控制的系统中。
【媒体推荐】
阿甘本的感觉、叙述和思考都特别迷人。
——《政治评论》
《神圣人》绝对值得一读,因为它独具启示性和挑战性。
——《现代派》
正是这部著作,使阿甘本正式跃升为世界性的顶级学者之一。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
◆“神圣人”生命政治系列的开篇之作
◆无可争议的政治哲学经典名著
【内容简介】
在《神圣人》中,阿甘本旨在把关于纯粹可能性、潜在性与权力的问题,同政治与社会伦理的问题在以下语境中连接起来:后者已丧失其早前的宗教、形而上学与文化的立基。阿甘本从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碎片性分析中获得启示,进而以巨大的广度、强度与敏锐度,在传统政治理论史中探查关于一种生命权力理念的隐秘在场。他指出,从政治理论的最早论题(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论述)开始,并且在整个关于主权(无论是国王还是国家)的西方思想史中,主权作为一种针对“生命”的权力的理念,始终隐秘存在。
阿甘本认为,这一理念始终保持纯然隐在的原因,在于神圣之域(或者说神圣性的理念)同主权的理念紧密关联的方式。阿甘本的研究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卡尔·施米特认为,主权者的状态乃是其所守卫的诸种规范的例外;人类学的研究已揭示神圣之域同禁忌之间的紧密交链。在此两者之上,阿甘本将神圣之人定义为那种能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人;在他看来,这个悖论性的人物恰恰仍活跃在现代个体的状态中——现代个体生活在一个对所有个体的集体性“赤裸生命”施加严密控制的系统中。
【媒体推荐】
阿甘本的感觉、叙述和思考都特别迷人。
——《政治评论》
《神圣人》绝对值得一读,因为它独具启示性和挑战性。
——《现代派》
正是这部著作,使阿甘本正式跃升为世界性的顶级学者之一。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
例外状态 豆瓣
Stato di eccezione
8.8 (20 个评分)
作者:
[意] 吉奥乔·阿甘本
译者:
薛熙平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 1
本书是阿甘本“神圣之人”系列的第三本作品,是对西方生命政治的历史—哲学考察计划的进一步展开。阿甘本继续延伸自己的语言—法律思维, 试图将“主权”的概念重新定位为“例外状态”的产物,一方面从回顾西方现代的例外状态史出发,上溯罗马法以考察其典范渊源,一方面则在施米特与本雅明的思想论战中思索翻转“例外状态”的出路,思索超越“权限”与“权威”之对立,打开一个新的政治行动空间的可能性。此次纳入“精神译丛”的简体字版由译者对原台湾麦田版的译文进行了全面修订。
诚然,例外状态今天已经达到其全球部署的顶点。法的规范面因此可以被一种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抹除与违背;而当它对外忽视国际法、对内宣告恒常性之例外状态的同时,却仍然宣称是在适用着法。
生存于例外状态之中,意味着同时经验这些可能性,但总是借由将两股力量(制法之力与废法 之力)分离,而不断尝试中断那正将西方导向全球内战的机器之运作。
——阿甘本
《例外状态》一书适时且令人折服地探索了国家权力撤回对于法律保障与法律权利之确保的能力,同时既将其属民弃置于法律暴力的即兴之下,又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我们不应将例外状态仅仅理解为偶发和限定的,事实上,引发例外状态已经成为建构现代国家权力的基础。阿甘本灵敏地思量这个权力的历史与哲学意涵,提供了关于“生命”和其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卓越思考。这是一本博学而挑战主流观点的书,呼吁我们“让机器停摆”,并且打破法对于生命所施加的暴力束缚。
——朱迪斯·巴特勒
诚然,例外状态今天已经达到其全球部署的顶点。法的规范面因此可以被一种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抹除与违背;而当它对外忽视国际法、对内宣告恒常性之例外状态的同时,却仍然宣称是在适用着法。
生存于例外状态之中,意味着同时经验这些可能性,但总是借由将两股力量(制法之力与废法 之力)分离,而不断尝试中断那正将西方导向全球内战的机器之运作。
——阿甘本
《例外状态》一书适时且令人折服地探索了国家权力撤回对于法律保障与法律权利之确保的能力,同时既将其属民弃置于法律暴力的即兴之下,又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我们不应将例外状态仅仅理解为偶发和限定的,事实上,引发例外状态已经成为建构现代国家权力的基础。阿甘本灵敏地思量这个权力的历史与哲学意涵,提供了关于“生命”和其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卓越思考。这是一本博学而挑战主流观点的书,呼吁我们“让机器停摆”,并且打破法对于生命所施加的暴力束缚。
——朱迪斯·巴特勒
敞开 豆瓣
L' aperto: L'uomo e l'animale
7.9 (14 个评分)
作者:
[意]吉奥乔·阿甘本
译者:
蓝江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2
人类历史的终结是一个事件,一个已经被从圣保罗到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从黑格尔到科耶夫的辩证学家所预言和宣告的事件。谁是即将来临(或业已降临)的走向终结的历史的主人公?人是什么?人如何登上舞台?然后人是如何在众多动物中成为主人和保持其首要地位的?
在《敞开》中,吉奥乔•阿甘本认为,人一直被看成自然的有生命力的身体和超自然的、社会的或神圣的因素的神秘结合体,我们反过来必须将人理解为把人性与动物性从实践上和政治上分开的结果。
从古希腊人和弥赛亚思想家,经由18世纪现代科学分类学和人类学的起源,再到20世纪人文主义的黄昏,阿甘本追溯了整个思想线索。他发现人的特殊地位是由西方思想中的“人类学机制”生产出来并加以巩固的。在古代和现代的版本中,人类学机制通过在人与动物之间制造一种绝对差异,让整个机制得以运转:一方面,让人凌驾在动物与环境之上;另一方面,相对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特质向一个世界的敞开而言,动物性从根本上被排斥在外。在阿甘本的考察中,他聚焦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区分之槛,这个状态既不是动物生命,也不是人的生命。这就是“赤裸生命”的状态。这个人类学机制一旦停止,就会为即将来临的哲学和政治铺平道路,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在《敞开》中,吉奥乔•阿甘本认为,人一直被看成自然的有生命力的身体和超自然的、社会的或神圣的因素的神秘结合体,我们反过来必须将人理解为把人性与动物性从实践上和政治上分开的结果。
从古希腊人和弥赛亚思想家,经由18世纪现代科学分类学和人类学的起源,再到20世纪人文主义的黄昏,阿甘本追溯了整个思想线索。他发现人的特殊地位是由西方思想中的“人类学机制”生产出来并加以巩固的。在古代和现代的版本中,人类学机制通过在人与动物之间制造一种绝对差异,让整个机制得以运转:一方面,让人凌驾在动物与环境之上;另一方面,相对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特质向一个世界的敞开而言,动物性从根本上被排斥在外。在阿甘本的考察中,他聚焦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区分之槛,这个状态既不是动物生命,也不是人的生命。这就是“赤裸生命”的状态。这个人类学机制一旦停止,就会为即将来临的哲学和政治铺平道路,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无目的的手段 豆瓣
Mezzi senza fine: Not sulla politica
8.3 (15 个评分)
作者:
[意大利] 吉奥乔·阿甘本
译者:
赵文
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
2015
- 1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是继《牲人》、《未来的共同体》、《没有内容的人》及《剩余的时间》之后阿甘本的又一力作,收录了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见于各处的文章。除了表达对舞蹈的蔑视之外,书中还出人意料地显示了对权利的虔诚渴望——《人权之外》:如果没有法与执法的结合体(即某种类似于国家的东西),权利是多么富有意义啊!除此之外,对“贝克特的梦与夜”的指涉也让让我们疑雾重重。
《没有目的的手段》紧靠吉奥乔·阿甘本那独一无二的躁动思想列车的一贯核心:在大屠杀之后,集中营将例外状态列入了国家主权的基本模式,考虑其遗留的影响,我们该怎样思考今日的政治?
在讨论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中,阿甘本那支柱性的矛盾化政治学依旧锐利逼人。这一点既反映在《面孔》中的对话(其中那位不明身份的谈话者据说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里,也见于作者对当代政治学——尤其是对意大利政治——所做的深刻个人思考之中。
《没有目的的手段》紧靠吉奥乔·阿甘本那独一无二的躁动思想列车的一贯核心:在大屠杀之后,集中营将例外状态列入了国家主权的基本模式,考虑其遗留的影响,我们该怎样思考今日的政治?
在讨论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中,阿甘本那支柱性的矛盾化政治学依旧锐利逼人。这一点既反映在《面孔》中的对话(其中那位不明身份的谈话者据说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里,也见于作者对当代政治学——尤其是对意大利政治——所做的深刻个人思考之中。
论再生产 豆瓣
Sur la reproduction
9.4 (20 个评分)
作者:
[法]路易·阿尔都塞
译者:
吴子枫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 7
阿尔都塞在五月风暴后撰写的重要手稿,其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由从中抽取的片段合成。本书在作者去世后出版,被认为是其最具体系性的文本,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作之一。本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的一系列经典主题,最核心的是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阿尔都塞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做出的论述,已被公认为当代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
我认为可以说,这个文本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是要描绘他的思想特征就必须参考的文本之一;是使用了烙有他自己名字的“印记”因而可被直接辨认出来的那些概念的文本之一;最后,它铭刻进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继传统中,成为当代哲学仍在继续研究的文本之一。——巴利巴尔
这部书稿首先是一份战斗性的教学文本,是阿尔都塞思想最理想的入门书,但它同时也一步步向我们展示了阿尔都塞独创性概念的加工过程。因此,它要求一种多层次的阅读:既把它作为包含着一个时代见证的政治文本来阅读,又作为以阿尔都塞式范畴来表达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阅读,还把它作为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唤问”功能的(新)理论来阅读。——比岱
自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最初提出以来,错综复杂的争论围绕着它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从而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复杂性,也暴露了它内在的各种难题。但是,对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可通约性这个直到最近的哲学还在提出的二难困境,这个理论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最有激发力的“解决办法”之一。就算这是路易·阿尔都塞在其不断变化而且涉猎广泛的全部著作中所做出的唯一的概念创新,他的名字也会牢固地树立在现代哲学史上。——詹姆逊。
我认为可以说,这个文本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是要描绘他的思想特征就必须参考的文本之一;是使用了烙有他自己名字的“印记”因而可被直接辨认出来的那些概念的文本之一;最后,它铭刻进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继传统中,成为当代哲学仍在继续研究的文本之一。——巴利巴尔
这部书稿首先是一份战斗性的教学文本,是阿尔都塞思想最理想的入门书,但它同时也一步步向我们展示了阿尔都塞独创性概念的加工过程。因此,它要求一种多层次的阅读:既把它作为包含着一个时代见证的政治文本来阅读,又作为以阿尔都塞式范畴来表达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阅读,还把它作为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唤问”功能的(新)理论来阅读。——比岱
自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最初提出以来,错综复杂的争论围绕着它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从而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复杂性,也暴露了它内在的各种难题。但是,对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可通约性这个直到最近的哲学还在提出的二难困境,这个理论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最有激发力的“解决办法”之一。就算这是路易·阿尔都塞在其不断变化而且涉猎广泛的全部著作中所做出的唯一的概念创新,他的名字也会牢固地树立在现代哲学史上。——詹姆逊。
临床医学的诞生 豆瓣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 une archéologie du savoir médical
作者:
Michel Foucault
译者:
刘北成
译林出版社
2011
- 1
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古典时代疯狂史 豆瓣
作者:
[法] 米歇尔·福柯
译者:
林志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 10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 福柯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做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他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罗兰·巴特尔
本书是福柯的早期巨著,曾以缩减本《疯癫与文明》风行知识世界。本书的翻译是直接源自法文的全译本,不仅还原了这部力作的原貌,而且能澄清许多因版本和译本原因辗转导致的许多争论与问题。
—— 福柯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做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他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罗兰·巴特尔
本书是福柯的早期巨著,曾以缩减本《疯癫与文明》风行知识世界。本书的翻译是直接源自法文的全译本,不仅还原了这部力作的原貌,而且能澄清许多因版本和译本原因辗转导致的许多争论与问题。